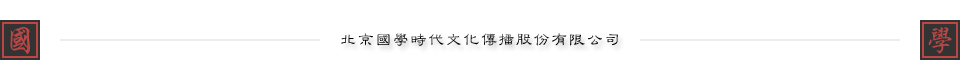从古希腊罗马史看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若干问题——《早期奴隶制比较研究》第一编第二章
第三节 奴隶占有制社会的等级阶级关系,自由民、奴隶主、奴隶;被保护民、隶农与公民以及奴隶的异同
脱胎于原始社会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占有制社会和国家,有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明显地表现为城邦时代和帝国时代两个大的阶段。无论在哪一个发展阶段,它们内部都有明显的等级阶级划分。无论在哪一个发展阶段,它们内部都是最高等级中的奴隶主执掌国家的权柄,利用国家机器首先维护本等级的特权。无论在哪一个发展阶段,等级划分都并非随时随地完全等同于阶级划分。
公元533年由查士丁尼颁行的《法学阶梯》,对延续一千多年的罗马国家的等级划分作了总结。其中指出:“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8]是自由人抑或是奴隶,这是古希腊罗马最基本的等级划分。
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还指出:“一切奴隶的地位没有任何差别;至于自由人则有许多差别,他们或是生来自由的,或是被释放而获得自由的。”又说,“从前,被释自由人分为三级”,即罗马公民、拉丁人和降服者。[9]
把自由人分成生来自由者与被释放而获得自由者两大类,这是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的重大特点。不同类型的自由人之间的关系,因时因地而异,对社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在自由民内部,从经济角度看,有奴隶主和自力谋生者的区别。而从政治方面考察,则存在有公民权者与无公民权者的严格划分。至于城邦时代的斯巴达内部,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完全等同于奴隶主。
在不同类型的自由民内部关系中,财富占有量的多少固然重要,但是在城邦阶段,特别是在城邦的早期,与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密切相关的公民权的重要性,胜过财富的作用。公元前451年雅典公民大会根据伯里克利的提议通过的公民权法,规定只有父母均为雅典人的人,才有取得公民权的资格。这个规定直到雅典城邦被马其顿人征服而丧失政治独立之日,一直有效。罗马国家境内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为了得到罗马公民权,与由罗马公民集体所体现的罗马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包括公元前90至前88年的同盟者战争那样的大规模武装斗争。
在雅典和罗马,无论是在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中,还是在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中,都是既有奴隶主,又有大量自力谋生的劳动者。在城邦阶段,国家政权主要操在有公民权的奴隶主手中。梭论改革时提出的按财产多少划分公民等第,不同等第的公民有权担任不同官职的规定,保证了富有公民即奴隶主对国家政权的控制。王政和共和时代的罗马,更是用制度保证了富有公民对国家政权的控制。
在古代雅典和罗马,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是不可能担任国家中的行政职务的。只有公民才有权占有属于整个公民集体即国家的土地。
在古代雅典,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由被释奴隶和定居雅典的异邦人构成。他们中的某个人,即使是拥有大量奴隶的奴隶主,他也不可能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起积极作用。既不可能参加公民大会,也不可能充当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于无权占有土地修建自己的房屋,他只能租房居住。他还要向由全体雅典公民体现的雅典国家交纳一定数额的人头税。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无权与雅典公民缔结合法婚姻。
在古代斯巴达,黑劳士和土地,由斯巴达公民集体占有,政权完全由斯巴达公民操纵。相对于斯巴达公民而言,边民只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等级。[10]他们对由斯巴达公民所体现的斯巴达国家,承担了提供辅助兵源的重要义务。他们中的富有者,可能拥有买来的奴隶。
在古代罗马,无论是在城邦阶段还是在帝国阶段,都有数量大大超过罗马公民总数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存在。他们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即被释放的奴隶,以及通过不同方式沦为罗马国家的被统治者而又没有被当作奴隶对待的广大人群。由于罗马国家长期广泛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同样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之间的不同集团的具体处境,可能千差万别。但相对于罗马公民这一拥有特权的等级而言,他们都是从属于统治等级的被统治者。在没有罗马公民权的自由人中间,不乏拥有数目可观的奴隶的奴隶主。
无庸讳言,虽然无论是在雅典、斯巴达还是罗马,在城邦时代,公民权的获得,首先取决于父母是否是该城邦的公民,换句话说,即仰赖于特定的血缘关系,但是,在公民的生活中,财富占有量的多少,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随着城邦的逐渐解体和进入帝国发展阶段,财富的作用不断增大。
就是在公元前7世纪末或前6世纪初通过所谓“吕库尔戈斯改革”(亦译为“来库古改革”)形成的斯巴达公民的“平等者公社”中,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个人发财致富,防止斯巴达公民中产生财产方面的不平等,但是,由于公餐制所要求的每个斯巴达公民按月从自己的收入中支付一定数量实物的规定,这实际上是把斯巴达公民权与每个公民的财产状况挂钩,随着岁月的流逝,由于每个斯巴达公民家庭人口数量不等之类因素,仍然使得一些无力按时交纳公餐制所要求的实物者失去公民权。斯巴达公民人数在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不断减少,就与这种公民权和财产的相互关系有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指出,由于斯巴达公民集体的分化,在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所谓“平等者”,已不是指所有的斯巴尔提阿特斯,而是仅指其中富有的部分。[11]
在雅典,从梭伦改革时起,即强调公民的权利与财产状况有关,规定只有富有公民才能担任最重要的行政职务。伪色诺芬在《雅典政制》一文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富有公民在雅典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去世后城邦内部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对待雅典公民中贫穷者的公民权以及与公民权有关的福利问题。如果说,公民大会于公元前451年通过的由伯里克利提出的公民权法,强化了公民权与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关系的血缘联系,那么,公元前411年政变的组织者安提丰、弗吕尼霍斯、特拉麦涅斯等人,则都力图使公民人数以5000名为限。也就是只允许富有公民行使参政权。同时废除了对担任公职者的补助。在公元前404年“三十僭主”当政时期,按照克里提阿斯的计划,只应有3000人享有公民权,并且颁布法令剥夺了公民以外的人的法律保护。[12]而按照著名古希腊史专家埃伦伯格估计,在公元前425年,雅典公民总数约29000人。[13]马其顿人在其使雅典人臣服期间,一再剥夺贫穷公民的公民权。公元前322年,规定拥有2000德拉赫麦的人才能有公民权。[14]公元前318年,卡山德罗斯又规定,拥有1000德拉赫麦者才能有公民权。[15]
在古代罗马的城邦时代,强调公民权、占有土地的权利和服兵役的义务三位一体,并且采取切实措施来维护这种三位一体的体制,使其免遭破坏。[16]这是罗马国家长期奉行的政策,也是国家能够不断扩张,终于成为地跨欧亚非的庞大强国,并且逐步演变为罗马帝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罗马国家凭借公民兵的集体努力,不断开疆辟土,将掠夺来的土地分给新增加的公民和土地不足的公民。每个公民必须忠实履行服兵役的义务。由于天灾人祸兵荒以及各家人口数目不同等等因素,公民中的贫富分化必不可免。公民中必然会不断出现无力履行兵役义务因而面临失去公民权的人。公民兵源的减少又会削弱罗马国家的国力。城邦时代的罗马,从来是靠公民兵作战斗的主力,从未像公元前4世纪的许多希腊城邦那样依赖雇佣兵作战。公元前2世纪末马略进行的军事改革,重要的客观效果之一就是,使贫穷的公民通过当兵能够重新获得土地,变成拥有足够财产的罗马公民,使罗马公民人数不致减少。
正是由于强调公民权、占有土地的权利和服兵役的义务三位一体,所以罗马国家从其建立的初期开始,争取土地的斗争,就与自由人中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利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这种斗争,构成延续数百年的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基本内容。[17]
罗马国家的一系列规章法令,从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制定的按森图里亚投票制度,到《十二铜表法》中关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的规定,从罗马行政官员的竞选和升迁办法,到占有土地最高限额的规定,无一不是首先保护富有公民即奴隶主的利益,维护他们的特权。 在奴隶占有制国家中,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和有公民权的自由人,虽然相对于奴隶而言都是自由人,但实质上,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整体上从属于公民集体所体现的国家,其中的许多人还分别从属于某个或者某些公民。从属关系的集中表现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对控制着他们居住地区的公民集体,单方面地承担服兵役、纳税等项义务,而不享受公民所拥有的多项权利。在数百年内盛行于罗马的公民与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便是这种从属关系的鲜明表现。希罗多德书中关于斯巴达国王治丧仪轨的记载,生动地揭示了边民从属于斯巴达公民集体。在安葬作为斯巴达公民集体的首领的国王的时候,一定数目的边民和一定数目的黑劳士一起,被迫到场充当哀悼者。[18]在这里,边民和黑劳士的社会地位是一致的。
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奴隶,居于奴隶占有制社会等级阶梯的最下层。他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由奴隶主供给衣食,另一类则同奴隶主分开居住,自谋衣食,但要向奴隶主交纳实物或金钱。[19]不论哪一类奴隶,人身都隶属于奴隶主。奴隶主或者个别地有权,或者只是集体有权任意处置他们的生命,更不必说任意处置他们的财产。从法律方面讲,奴隶的一切财产均属于奴隶主。奴隶所使用的土地,不言而喻,或属于个别奴隶主,或属于奴隶主集体。
以前经常存在一种情况,即不少研究者在分居奴隶的等级阶级属性问题上争论不休,最根本的原因是把“人身占有”与“人身依附”混为一谈。在斯巴达、雅典和罗马这一类直接从原始社会废墟中产生的奴隶占有制国家里面,“人身占有”的主要根据是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内外划分。通过禁止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法律,使只能对其他氏族部落的成员实行人身占有变成十分明显的事实。在每个人的等级阶级属性,即他是一个自由人还是一名奴隶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主要取决于他的氏族部落归属的城邦时代,剥削和奴役,只能通过人身占有来实现。不全面地考察城邦时代等级阶级关系形成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当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单纯看被剥削的劳动者,特别是从事土地耕作的劳动者是否自谋衣食,并据此来断定他们的等级阶级属性,难免产生认识上的偏差。
为了正确理解奴隶占有制社会的等级阶级关系,有必要对被保护民和隶农的情况作简略的考察。
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需要有公民权的自由人的保护,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古代罗马,保护人与被保护人关系得到特别广泛的发展。
从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这个角度看,被保护民与奴隶一样,相对于公民集体而言,他是“外来者”。另一方面,与奴隶不同,被保护民的自由人身份得到由公民集体所体现的国家的承认和保护。
隶农作为自由民中的一个等级,主要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形成并获得广泛发展。就这一等级的发展主流而言,乃是奴隶占有制国家日益加速地打破氏族部落血缘关系的狭隘界限,依据地缘和财产状况来确定自由人的法律地位的过程中,享有罗马公民权的自由民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逐步下降和恶化的结果。根据公元4—5世纪罗马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原本享有完全公民权、根据契约租种土地的一些承租人,失去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其本人以及家庭财产构成所在庄园财产的一部分,土地所有者成为他们的主人。与奴隶不同,法庭仍然承认隶农是自由人。隶农之从属于大土地所有者,首先是因为他缺乏土地。罗马国家之所以要颁布一系列法令迫使他们固着于土地上,是因为劳动力的流动和丧失,严重影响财政收入。
第四节 早期奴隶占有制国家的发展趋势:斯巴达、雅典、罗马
前文我们主要从社会和政治结构,对斯巴达、雅典和罗马三个奴隶占有制社会和国家,作了概略的考察,而且主要是剖析它们在城邦发展阶段的等级阶级结构。
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虽然与历史传统、地理环境以及周围的部族或国家的相互关系,都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但最主要的是一定经济关系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例如在斯巴达,由于一系列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按照俄罗斯古希腊史专家Ю·Β·安德列耶夫的说法,“城邦制度的一些特点在这里得到极端的、也可以说是精巧和奇妙的发展。”其特点是斯巴达“以确认‘共同的私有制’原则,建立起经过周密考虑和仔细拟订的对公民日常生活实行直接监督的制度,首先是对他们消费由受奴役的黑劳士的劳动所提供的产品实行监督。落后的农业经济占据优势,经常面临被奴役居民的起义,被奴役者人数又超过斯巴达公民许多倍,在这样的条件下,这种制度无疑是保持公民集体团结一致最简便和合适的方式”。[20]在斯巴达这种类型的奴隶占有制国家中,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斯巴达公民集体与作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阶级的对立是十分明显、十分尖锐的。阶级对立与等级对立完全一致。在这种国家中,等级之间的界限,首先是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斯巴达国家长时期尽力强化公民与黑劳士之间的等级阶级对立。
作为斯巴达公民集体利益体现者的国家,通过规范公民和非公民的生活行为准则,达到强化等级阶级对立的目的。
埃弗拉伊姆·达维德的《斯巴达社会中的笑》一文,从一个侧面深刻揭露了斯巴达国家强化等级对立的良苦用心。文中指出:“在斯巴达,笑被当作强化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工具”,“国家对其公民的笑实行控制的程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即对他们何地、何时、何故以及以何种方式发出笑声,都实行监督”。[21]
强化等级制度的结果,必然是使斯巴达这样一个由原始社会的基于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的人群集团演化成奴隶占有制国家中的统治阶级,成为完全排他性的封闭的等级,最后只能走上人数日减而终被外邦灭亡的道路。公元前192年,斯巴达因在战争中失败而被迫加入长期与其敌对的阿哈伊亚同盟。当时统治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地区、并且在打破邦际狭隘界限方面有所作为的阿哈伊亚同盟,于公元前188年明令废止了黑劳士制度。[22]
雅典在它作为政治上独立的奴隶占有制城邦存在的整个期间,内部的等级阶级界线也十分鲜明,只是不像在斯巴达那样绝对不可逾越。无论是在梭伦改革时期,还是在克利斯梯尼改革时期,都曾有过把非雅典人登记为雅典公民的现象。就是在公元前451年公民大会通过伯里克利提出的公民权法之后,通过公民大会的决定而接纳非雅典人加入雅典公民集体的事,也间或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一个名叫帕西昂的奴隶,就曾获得雅典公民权,成为名噪一时的富翁。不过,就事物的主流而论,雅典公民集体的闭塞性是很强的。这就使得它的公民总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达到创记录的约4万人之后,只能长期在2万至3万之间徘徊[23]。雅典依靠公民兵的力量,不可能抵挡住马其顿人的侵略,终于被马其顿人灭亡。
作为奴隶占有制城邦的罗马,从其建邦时起,在公民权问题上也遵循血缘原则,即只有经过合法婚姻出生的罗马公民的后代才能取得罗马的公民权。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罗马国家在维护公民,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和奴隶三个大的等级划分的格局的同时,为公民以外的两大等级的成员进入公民等级,提供了不少方便条件。从而使公民的人数不断增加,保证了罗马的疆域在数百年内持续扩张。罗马之所以从地处台伯河畔的一个小邦能够发展成地跨欧亚非的庞大奴隶占有制帝国,它的成功的公民权政策,不能不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正是通过不断变非公民为公民这个重要手段,罗马国家才消灭了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在形成人们的等级阶级属性方面的决定性作用。逐步使财产和地域原则在确定特定的人的等级阶级身份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显示出不断增大的作用。关于这方面的详情,涉及整整一部罗马史,这里不能细说。
公元211—217年当权的罗马皇帝卡拉卡拉于211年颁布的著名敕令,无疑是罗马帝国境内公民与非公民界限逐渐泯灭的重要见证。饶有兴味的是,敕令中称所有尚未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人为“异邦人”。[24]英国著名学者A·H·M·琼斯在《晚期罗马帝国(284—602)》一书中评论卡拉卡拉211年的敕令的意义时指出,该敕令至少是加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方面,形式上消灭了帝国内部的所有地理上的区别,使布里吞人和埃及人与意大利人一样成为罗马人。至少到4世纪,行省人自认为罗马人。一个人无论是住在高卢还是住在意大利、色雷斯或卡帕多西亚,他都有同样的升迁机会。另一方面,它确认了社会的上层等级和普通民众法律上的明显区别,并使这种区别具有普遍的性质。普通民众被贬低到往昔的异邦人的相似地位。[25]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只是应该补充指出,按照过去的罗马公民权法,布里吞人、埃及人之所以区别于有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人,首先不是因为他们住处不同,而是从理论上追溯他们祖先的血缘,他们与已被接纳进罗马公民集体的人有别。
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变成地跨欧亚非的庞大奴隶占有制国家时算起,到卡拉卡拉敕令颁布时止,在300多年的时间内,罗马国家不仅完成了从共和制向帝制转变,而且在帝制的基础上又走了很长的路。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罗马国家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情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阶级等级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阶级等级关系而言,概括地说,基本的变化是,旧的源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的各种狭隘界限,逐步被打破并趋于消失,分属于不同部族的富有的奴隶主阶级融合成帝国内部统一的统治阶级,共同组成罗马社会和国家中的上层等级,剥削压迫广大的贫苦民众。取代以往公民和非公民区别的是所谓“尊贵者”(Honestiones)和“卑贱者”(Humiliores)之间的日益加强的差别和对抗。[26]
在经过激烈动荡的“3世纪危机”之后,到公元4世纪,开始了罗马帝国政府大力推行把隶农固着在大地主的庄园的土地上的时期。隶农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急剧恶化,名为自由人,实际生活接近于奴隶。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和无公民权的自由人混合为一,实际上都在失掉自由,成为一身二任的大奴隶主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压迫对象。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正在走向崩溃。[27]
反映属于日耳曼人一支的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以后的时期内的社会制度的重要文献,于5世纪末或6世纪初编纂的萨利克法兰克人的法典《萨利克法典》,从一些方面说明,正在形成中的封建制度,与一度存在于斯巴达、雅典和城邦时代的罗马的奴隶占有制度,有多么鲜明的区别。
例如,法典规定,劫走或者杀死负有纳税义务的罗马人,应罚付63金币,而杀死作为国王奴仆的男爵或副伯爵,应罚付300金币。[28]法律明显地保护村社的权利,规定如有人要迁入别的村庄,即使是一个人出来反对,他就不得迁入。[29]法律中还有“关于愿意脱离氏族关系”的专门条文。[30]
注释:
[1] 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曾经指出:“全部传说的罗马上古史都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这种黑暗又因后世受过法学教育的著作家们(他们的著作还是我们的材料来源)的唯理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和报告而更加浓厚。”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46页。20世纪初一度流行于史坛的超批判流派,覃是彻底否定古代作家关于罗马早期历史的记述,认为关于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事件的记载,全系不可信的传说。在1988年出版的《欧洲史》第1卷中,前苏联古罗马史专家И·А·马雅克指出,具有客观性的考古材料建立了罗马远古历史的可靠框架。只要综合运用考古学、语言学和文献史料,就可以基本弄清古代罗马早期的历史。参阅《История Европы》,Том первый,Древняя Европа,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8,第l83页。
[2] 参阅拙著《关于奴隶占有制社会的一些思考——<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一书读后》,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第57页以次。
[3] 集中反映上述两位学者对黑劳士问题的主要论点的论文,载于1988年出版的《奴隶制和非自由劳动的其他一些形式》(Slavery and other forms of unfree labour,Edited by Léonie Archer,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一书,即 G.E.M.de Ste Croix,Slavery and other forms of unfree labour以及Paul A.Cartledge,Serfdom in Classical Greece,
[4] 关于斯巴达的黑劳士的等级阶级属性问题,请参阅刘家和的论文《论黑劳士制度》,载《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三联书店,1982年,第167—221页。对于由被称为“斯巴尔提阿特斯”(Spartiates)的斯巴达公民所组成的斯巴达国家说来,黑劳士全系属于不同的氏族部落的被征服者,即本氏族部落以外的“外来者”,这就是决定黑劳士的奴隶命运的关键。征服者可以随意把被征服者变为奴隶,这是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习俗。
[5] 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i Historiae,recognovit brevique adnotatione critica instruxit Carolus Hude,Editic tertia,Oxonii),I,151。
[6] 同上书,Ⅵ,32。
[7] 关于公民集体等同于国家的问题,请参阅埃伦伯格所著《希腊人的国家》(Victor Ehrenherg,The Greek State, The Norton Library,W.W.Norton and Company.INC.New York,1964)一书的第二章。
[8] 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北京,第12页。
[9] 同上书,第12、14页。
[10] 关于斯巴达边民等级形成的历史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请参阅P·卡特利基所著《斯巴达和拉科尼亚》(Paul Cartledge,Sparta and Laconia·A regional history 1300—362BC,Routledge and Regan Paul,London,1977)一书的第7和第10两章。
[11] 关于斯巴达公民集体内部的分化情况,请参阅前引P·卡特利基所著《斯巴达和拉科尼亚》一书的第14章;Л·Г·佩怡特诺娃的文章《吉波麦伊奥内和莫法基(斯巴达公民集体的结构)》(Л.Г.Печатнова,Гипомейоны и мофаки(Структура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коллектива Спарты),载《古代史通报》,l993年第3期。
[12] 关于公元前411年和404年在雅典发生的两次反民主政变的详情,请参阅1956年出版的由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集体著作《古代希腊》(Древняя Греция,Ответственнные редакторы В.В.Струве,Д.П.КаΛΛистов,ИздатеΛъство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Москва,1956),第327—347页。
[13] 参阅前引埃伦伯格著《希腊人的国家》,第33页。
[14] 参阅А·Б·拉诺维奇著:《希腊化及其历史作用》(А.Б.Ранович ЭΛΛинизм 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роΛъ цздатеΛъствс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Москва—Аенинград,1950),第84页。
[15] 同上书,第87页。
[16] 关于罗马公民权问题,请参阅l96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С·Λ·乌特钦科的专著《罗马共和国的危机与衰亡》(С.А.Утненко,Кризис и адение Риμской РеспубΛики)的第7章。该章译文见《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北京,第231—267页。
[17] 在古代罗马的历史上,“平民”(plebs)一词的意义前后有过重大变化,在王政早期,平民是罗马国家境内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由于罗马公民集体所体现的国家在与四邻的频繁战争中,极端需要他们充当重要兵源,因而在起自王政时期而终于共和时期的漫长斗争中,不得不向他们作出让步。结果是,早期的平民与贵族融为一体,成为统一的罗马公民集体的成员,两者一起组成新的罗马公民集体。这是罗马国家发展史的一个突出而且十分重要的特点,也是罗马公民集体一定程度开放性的重要表现。
[18] 希罗多德,《历史》,Ⅵ,58。
[19]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就提到过在日耳曼人中存在“奴隶只纳贡,不服任何劳役”的现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58页。
[20]参阅《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109—110页。
[21] 埃弗拉伊姆·达维德:《斯巴达社会中的笑(Ephraim David,Laughter in Spartan Society),载论文集《古典时代的斯巴达:它的成功背后的诀窍(Classical SpartatTechniques Behind her Success,Edited by Anton Powell,Routledge, London, 1989),第17页。还可以参阅该论文集的前言以及第26页以次。
[22] 参阅P·卡特利基:《斯巴达和拉科尼亚》,第322页。
[23] 关于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雅典公民人数的变化情况,可参阅埃伦伯格:《希腊人的国家》,第33页。
[24] 参阅由B·B·斯特鲁威主编的《古代世界史选读》第3卷(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его мира Под редацией В.В.Струве том Ⅲ 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Москва,1953),第242页。
[25] A·H·M·琼斯:《晚期罗马帝国(284—602)》(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A social, economical,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volume l,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1986),第17—18页。
[26] 根据琼斯的说法,“尊贵者”与“卑贱者”之间的区别,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即已出现。参阅琼斯,前引书,第17页。还可参阅格查·阿尔费尔迪,《罗马社会史》(Géza Alf☆ldy,The social history of Rome,Translated by David Braund and Frank Pollok,Routledge,London,1988),第106—202页。
[27] 关于“三世纪危机”之后罗马帝国内部的变化,参阅前引《欧洲史》第1卷,第639页以次。
[28] 参阅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年,第22、26页。
[29] 同上书,第24—25页。
[30] 同上书,第28页。
文章分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