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
五、筦榷之利: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及其长远意义
刘安《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南征百越,乃“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汉书·地理志》谓:汉武帝遣译长航向黄支,目的之一为“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可见秦汉经略南海,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海外珍物,以供宫廷消费。1982年,南越文帝陵出土了镂孔熏炉、象牙、乳香、圆形银盒、和金花泡饰等与海外交通相关的珍贵遗物,显示贸易与南越宫廷消费的关系。当然,不应该排除海外贸易对国家财政的意义。六朝时期,地方官府作法兴利,对贸易实施专卖,获取利润,以为上供与补助地方财政。史载梁代广州“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1]
唐代海外贸易空前高涨,朝廷在广州创设市舶使,管理东南海路通商,一方面为内库开拓财源,另一方面也为朝廷收购海外珍异;地方政府则通过参与贸易管理,获得财源。安史之乱后,为改变财政紧张状况,唐朝推行两税法,把正税划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保证中央财政收入;另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盐、茶、酒等行业实施专卖经营,对海外贸易开征“舶脚”,开拓工商税源;市舶之利通过内藏渠道资助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刘蜕《献南海崔尚书书》云:“南海实筦榷之地,有金珠、贝甲、修牙、文犀之货。”[2]市舶之利对国家财政如此之重要,以致于乾符六年黄巢攻占广州求为岭南节度使时朝议反对之声甚强烈,左仆射于琮云:“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3]
南海贸易的重要性无论对于南汉皇室消费、内库财源乃至国民经济,都是毫无疑问的。兴盛的南海贸易确实为南汉带来十分丰厚的市舶收入。高祖刘岩时,外贸日盛,“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4]后主时,“珠贝、犀象、瑇瑁、翠羽,积于内府,岁久不可较。”[5]
后唐同光三年,庄宗伐蜀,平之,得钱粮数百万,另有金银22万两,珠玉犀象2万。[6]吕思勉先生认为这些珠玉犀象与南海贸易有关,“盖亦自交、广来者。”又《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谓钱氏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亦可见其物之北上者不少。”[7]
由于厚利所在,对外贸易成为刘氏立国的重要资本。前引宋神宗给发运使薛向、副使罗极的手诏,所谓“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有笼海商得术也。”[8]说明吴越钱氏和南汉刘氏重视对外贸易,都获得可观的回报。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称:“宋兴,而吴、蜀、江南(南唐)、荆湖(南平)、南粤(南汉),皆号富强。”[9]明代学者王夫之云:“钱氏虽僻处一隅,非宋敌也,而以视江南(吴、南唐)、粤、蜀,亦足以颉颃而未见其诎。”[10]南汉跻身五代强国行列,相当程度靠对外贸易的支持。
宋太祖赵匡胤甫定荆湘,即对其弟赵炅说:“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11]广南、江南的经济优势,海外贸易即居其一。所以,开宝四年宋平南汉,即派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欧阳炯祭南海(炯未至,该以司农少卿李继芳),以广帅潘美、尹崇珂并兼市舶使,通判谢玼兼判官,管理海外贸易。
研究中国中古社会的中外学者早就敏锐地注意到,由中唐至宋,中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革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经济结构有所松动,城市与商业及其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尤其是宋朝把发展商业贸易上升到国计民生决策高度,实施“通商惠工”政策,确实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变局。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把唐宋社会变革与欧洲近代化进程相比较,提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命题。[12]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Gernet,1921—)比较宋元明三朝经济结构后说,14世纪的国家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宋代国库的大部分是由经商税所维持,而商业经济在蒙古人统治时代仍保持着一种重要性,那麽国家的主要收入此后就将由农民提供了。”[13]海外贸易在国计民生的重要是不可忽视的。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14]据汪圣铎先生研究,北宋淳化、皇祐、治平年中,市舶课利在50—60余万株颗之间;元符年间,每年收入约41万余;崇宁、大观年间收入激增,十二年共收入1000万,每年平均111万;南宋绍兴二十九年以前,岁入更达到200万。[15]可见商业贸易及其税收在宋代国家财政与经济中是何等的重要!
处在唐宋两大辉煌王朝之间的五代十国,在动乱分裂后面,涌动着不易觉察的社会经济变革的新动向,南汉、闽、吴越等濒海国家活跃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带有“贸易立国”的开放取向与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大异其趣,不自觉地担当起唐宋“社会变革”和“经济革命”承前启后的桥梁。杜希德、思鉴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值得注意:印坦沉船所载的货品是一个大规模国际贸易网络的生动例证;在宋中晚期及元代出现一个组织完善且规模更大、支持南部中国制造和外销产品的产业经济相当部分的海上贸易网络之前,也就是10世纪后半段,这些经济发展已经在南汉启动。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有点遗憾,迄今为止,中外学者由于热切关注了两头(唐和宋),往往忽略了中间(五代)。



印坦沉船上发现的铭文银锭、带封套的银锭、南汉铅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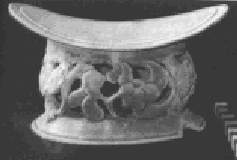
印坦沉船上发现的定窑白瓷碗残片、繁昌窑斗笠碗、越窑瓷枕。(杜希德(DenisTwitchett)、思鉴(JaniceStargardt):《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闽国刘华墓出土孔雀蓝釉瓶(《福建文博》1999年第2期)

广州番禺大学城“康陵”出土玻璃瓶(今存广州市博物馆)
注释:
[1]《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
[2]《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九;亦见《白孔六帖》卷八十三《商贾》。
[3]《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八《郑畋传》。
[4]梁廷枏:《南汉书》卷十《黄损传》。
[5]路振:《九国志》卷九《邵廷琄传》。
[6]《旧五代史》卷三十三《唐庄宗纪》
[7]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07页。
[8]李焘著、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宋神宗熙宁二年七月壬午。
[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考·历代国用》。
[10]王夫之:《宋论》卷二《太宗》。
[11]王称:《东都事略》卷二十三《刘鋹传》。
[12]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第10-18页、第153-242页。
[13]谢和耐(JacquesGernet)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第339页。
[1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三。
[15]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723-7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