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家庭消费——《中国家庭史》第四卷第三章第四节
二、食
“民以食为天”,食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大概谁也不会表示怀疑,在家庭中也不例外,当时谚云: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1]即将以上七件事视为·个家庭维续首当其冲的要素,而这七件事无一不是关乎饮食的[2]。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当时家庭中饮食消费要占到总生活支出的76%以上,其中又以主食的消费最为重要,占食物消费的三分之二左右或更高。那么当时人主食消费量如何呢?关于这一问题,史料中很早就有“日食·升”的说法,这在明清时期也很普遍。比如,明代关于廪生的口粮标准就是“日米一升”[3]。清初的靳辅在上疏中也说:“每人每日食米一升。”[4]乾隆间的洪亮吉则言:“今时之民,约老弱计之,日不过食一升。”[5]这应该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沈氏农书》中在计算长工的工食时说:“一年中牵算,每人一升五合,妇人半之。”[6]这是指成人,一夫一妇2.25升,若与小孩牵算,大致也为1升。由此可见,文献中常常提到的“日食一升”是指包括老人孩子在内的家庭人口的平均食量,而一个正劳力,即成年男子的食量大约为一日一升五合。若按此计算,则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则需消耗食米l8石,相当于1800斤。当然,这是指可以管饱的食量,实际上,许多家庭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比如清初曾任给事中的福建晋江人王命岳,在出仕前,家境颇为困难,有祖父、父母及弟妹约十人,全家每天早中两餐各食米二升五合,晚饭吃一升五合,合计六升五合。就这,还不能全然保证,所以,他母亲常常处于半饥半饱状态[7]。由此大概可以看出,如果能保证平均日食一升的水平,应该算比较理想了。当然,食米多为南方人的习惯,在北方多以麦、高粱和小米等为主。比如,在山东广饶县,“饮食,五谷皆有,夏多食麦,冬多食高粱,杂以黑丽,春秋问用小米”[8]。山西代州“民食以粟为主,佐以荞麦燕麦,贫者黍菽即为珍膳,有终岁不识膏粱之味者”[9]。河南密县“大率民间常食小米为主,以黄豆及杂粮佐之,其大米饭小麦面俗所珍惜,以供宾粲之需,非常食所用”[10]。可见,米和麦虽然一般可分别视为南北方的主食,但在北方,麦却非一般家庭的常用之食,麦被视为细粮,大概只有中上之家可以经常食用,普通人家只是在节日或招待宾客时偶一用之,日常食用多为高梁、粟乃全糠菜等粗粮。比如,直隶望都县,“上中之户所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掺糠和菜为食,……小麦面粉皆不常用,麦秋后家家食麦面数日,籍酬农工之劳。过节度岁亦食之,余者收藏备粜以为度日之费,R常食用亦小米为主要食品。”[11]南方的情况,特别是江南,情况可能要好于北方,但大米显然也不足那些贫苦家庭常年能够食用。明代杭州的田艺蘅曾言:
而大米,北人不常得食,极边最为贵重。今南人穷者乃食大小麦、荞麦、黄黑豆、蚕豆、稷粟,尽食之尤不足以充腹。[12]
而至于灾荒之年,树皮、草根也就成了贫民相当不错的食物,甚至一砦士绅地主家庭,也会以此为食,苏州的王永年曾记录下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艰苦生活:
(咸丰)十年及十一年春,升米价须大银二百文,甚至有钱无买处。某日,由友引至程阁老巷某姓宅,买得一升袖归。俟夜半,以小钵煮其一合,供小儿承钰之一饱,真苦境也。至于苜蓿充饥,麸皮供饱,岂止一朝一夕已哉。野菜中,仅苜蓿、磨盘菜、灰条菜尚可适口,此外则土味兼野草气,殊难下咽。其苦如是,今书至此,泪尤涔涔下也。[13]
不仅如此,在树皮草根都无处刈觅的情况下,有一种被称为“观音粉”的白色的软石,也成了人们的食物。比如,乾隆二十年(1755),江南大灾:
明年丙子春,流民争望烟而集,时称饿虱,沿乡村至无敢午炊者。山间草根树皮都食尽,有观音粉一种,是山石所化,食之能害人,饥民迫于充饥,即官禁弗能止也。[14]
这种观音粉取自某种山石,这种石头“出粉白而腻”,民人取来后,“用砂糖沸汤调食,可以疗饥。有搀一五谷而服者,亦无恙,单食此粉,多致肠实,大便壅塞而毙。”[15]更为悲惨的是人相食,清代的扬州著名学者焦循曾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人相食的凄惨景象,至今读来仍让人心酸不已:
未死不忍杀,已死不必覆。出我橐中刀,刳彼身中肉。瓦鬴烧枯苗,煎煎半生熟。赢瘠无脂膏,和以山溪蔌。生者如何救,死者亦甘服。此即妻与孥,一嚼一号哭。哭者声未散,满体乍寒缩。少刻气亦绝,又满他人腹。[16]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当时还存在着公然出售人肉的现象:
同治三四年,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后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指溧水、溧阳——引者),八十文一斤,惨矣。[17]
副食方面,按前面谈到的谚语中可以看到,几乎与现代一样,油盐酱醋为当时必要的调味品,这些东西,从《补农书》等资料来看,除了盐以外,农家大多采取自制的方式,应该多少可以置备,不过像油,虽然现代有的菜油、麻油、豆油等品种当时均已存在,但相对于其他调味品来说,显然比较珍贵,所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比如田艺蘅指出:“香油贵时,则熬猪油而食之,惟徽州人四时皆食之。深山穷谷,近如于潜、昌化一路,不能得油,则取饭锅米汤以炒菜,名日米油,其穷甚矣。”[18]至于蔬菜,总体上看,南方因为物产等方面的原因,似乎要较北方讲究,品种也相对丰富,在北方,大抵“一年之中,春冬以菜蔬红薯白菜、夏秋以萝卜北瓜等物为菜羹,用以佐食”[19]。而目.常常有“鱼肉惟之宴会用之”、“贫家终年不见肉”之类的记载[20]。而在南方,特别是在江南地区,由于气候适宜,不仅蔬菜的品种较多,而且种植和培养也相对容易,所以一般家庭食用应该不会困难,而且吃荤的机会也应远较北方为多,特别是鱼之类,只要出功夫,便不难从河中捕捞。这一点,从《沈氏农书》关于长工的饮食安排中便不难看出:
旧规:夏秋一日荤,两日素。今宜间之,重难生活多加荤。
春冬一日荤,三日素,今间二日,重难生活多加荤。……
旧规:荤日鲞肉每斤食八人,猪肠每斤食五人,鱼亦五人;今宜称明均给,于中不短少侵克足矣。
旧规:素日腐(指豆腐——引者)一块,值钱一文;当年钱值银九毫,豆一石值价五钱。今钱价、豆价不等,岂得尚以旧例行之。今后合与人人吃腐,不须付与腐钱,而多与油水,令工人勤种瓜菜,以补其不足。[21]
农忙季节能够每两天中有一天吃荤甚至天天吃荤,农闲季节也能于每三天中一天吃荤,而且即使吃素之日,每天也能够吃到一块豆腐,这与前面北方的有关记载相比,优势十分明显。这是明末的情况,而到清末,情况似乎还有所改进。据晚清苏州陶煦的《租覈》记载,当时雇佣农工,吃荤的天数较《沈氏农书》中的规定还稍有提高,“夏秋日总二十日荤,春冬总十日荤”。荤也不再用猪肠而用肉,肉一斤食四人,而且,“余日亦不纯素,间用鱼”[22]。当然,以笔者的体验,在农村中,雇工的饮食无疑要好于自家日常的饮食,因此,我们显然不能将此视为当时普通家庭日常的饮食水平。不过从当时一些记载中还是多少可以看出,肉虽然不是南方特别是江南普通家庭可以食用之物,但也绝不稀罕。比如,明代福建的谢肇涮说:
今执亲之丧,不饮酒食肉者罕矣。百日之内,禁之可也,过此恐生疾病,少加滋味,亦复何妨?至于预吉事,赴筵席,则名教之罪人也。江南之人,能守此戒者,亦寥寥矣。[23]
按上面的说法,江南之人吃肉乃是经常之事,若长期禁止,还可能导致生病的危险。当然,谢指的可能是官绅地主阶层,不过从下面这些穷人的故事中,应该可以看到,当时江南普通家庭不时食肉是可能的。比如:
严斗林,三岁丧父,母朱苦志纺织,斗林拾薪以养。十一岁,母病瘫痪,斗林无可为计,乃求乞得食,辄驰归奉母。稍长,佣工得值,时买酒肉进之。[24]
闽吴某居上新河,本宦家子,幼失怙恃,家道中落,贫无以自存。母素有一婢,极贤淑,以主家沦丧,藐然一孤,誓志不他适,独肩抚育之任。赁敝屋数椽,衣食之资,惟十指是赖。……逮吴成立,性喜绘画,苦无力从师,每过装潢所,见壁上丹青,辄心领神会,流连忘返,归而摹写之,人物山水各擅其长,遂卖画自给。囊有余钱,市肉归,以半供老姐姐,老姐姐必留以供吴飨。问其故,婉辞日:“予不惯食肉,汝劳心学画,食之当更益精神。视予食,尤乐也。”[25]
又如,在前而举过的一个案例中,福建龙溪县田阿荣,有两个儿子,平日靠砍柴度日,生活艰难,有一天,天下雨,没去砍柴,就一家没吃饭,到下午,他妻子拿了一床夹被到街上押了三升米。但就是这样,他妻子此前不久还曾“买来四两肉吃”[26]。以上这几个家庭显然都应属于当时的贫困家庭,肉对他们来说,一方面无疑是很珍贵的,但另一方面也不是常年难得一食。若是普通家庭,情况自然会更好一些。
副食中自然还包括饮料,当时的饮料主要包括茶和酒。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喝茶的历史,明清时期,喝茶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习,从明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茶也成为一种常见的待客之道。以致当时的民谚也把茶视为开门七件事之一。南方相当多的地方产茶,在产茶区,农家大可自制茶叶。不过,北方产茶地区较少,喝茶的风气也不如南方盛行。总体上,这方面的消费在当时普通家庭的消费中应无足轻重。而酒的消费则相对重要一些,《沈氏农书》和《租覈》在计算雇工的成本时,都列出酒一项。比如《沈氏农书》中说:

旧规:不论忙闲,三人工酒一杓。今宜论生活起:重难生活,每人酒一杓;中等生活,每人酒半杓;轻、省、留家及阴雨全无[27]。
而《租覈》中每年每个雇工酒的预算是二千钱,差不多相当于三分之二石米的价格。可见不属于微不足道的开支。对待佣工如此,在家庭中,酒也同样为日常之需,比如,在江西会昌,“每饭必先饮酒,虽贫民无不挈瓶而沽。客至,肴馔不必精美,若无酒以供,或食以劏粥,人辄以为慢客。”[28]北方,虽然平常的饮食较为节偷,但饮酒的风气却十分盛行,很多地方,“多嗜酒”,“虽穷乡僻壤,皆家有藏酒”,而且还“酒馆林立”[29]。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喝茶、饮酒不仅限于家庭之内,在日趋繁兴的茶馆、酒肆中的消费也逐渐成为相当多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据王鸿泰对明清城市的酒楼、茶馆的研究,明清不断兴盛的酒楼和茶馆的发展,意味着饮食空间由“日常性”饮食向“非日常性”的娱乐休闲方向发展的倾向,而从“酒楼”到“茶馆”,则显示其休闲性的趋于日常化、普及化[30]。而且,实际上它们并不仅大量出现在通都大会以及县城,在相当多的市镇甚至村落也颇具阵势,比如无锡的黄卬在乾隆时称:
酒馆、茶坊昔多在县治左右,今则委巷皆有之,传闻某处有佳点佳肴,则远近走赴。……至各乡村镇亦多开张,此则近在数年以内。[31]
海盐的胡穰园则指出
茶坊,乾隆初年,无有也,邑城只有县前及码头有之,亦不甚闹。自后城中渐有增设,既而市镇亦有之。今(指咸同间——引者)则所在都有,凡村落之有桥亭者,无不然也。[32]
注意的是,这些酒店茶肆的消费者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达官贵人或富商豪绅,而更多的是包括农民在内的普通民众。道光年间,吴县的潘曾沂,为课农区种,常往返于城乡之间,每次“早往则农未起,稍迟则尽入茶坊矣”[33]。在璜泾,“自嘉庆以来,酒肆有四五十家,茶肆倍之。乡民人市,饮酒之外,无不喝茶者”[34]。前述之海盐,“附近乡农始则乘无事而闲坐其问,既而习为常而忘所有事”[35]。显然,收费不高的一般茶馆和酒楼甚受普通民众欢迎,成为他们劳作之余一种难得而所费不多的消闲和娱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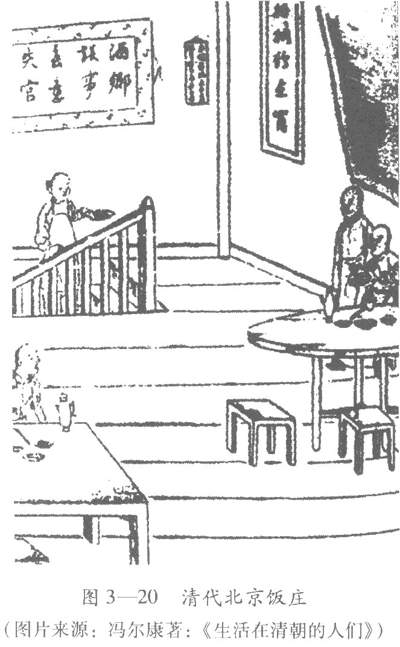
当然,考虑到当时的人口众多,茶馆、酒楼的生意虽然火爆,对于多数民众来说,大概也不过偶一为之。但这种行为的存在至少提醒我们,尽管在并不富裕甚至较为贫困的条件下,普通家庭成员也自会以富人看来也许十分廉价的方式找到自己的消遣和快乐。
注释:
[1]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十六《七件事》,上海古籍出版社l992年版,第481页。
[2]柴当然不能吃,但它主要功能是炊事。
[3] 《明会典》卷七十六《礼部·贡举-廪馔》,四库全书本。
[4]靳辅:《生财裕饷第一疏》,见《切问斋文钞》十五,转引自张研:《清代家庭结构与基本功能》,载《清史研究》l996年第3期。
[5]洪亮吉:《卷施阁q|集》卷一,第6b一7a页,《洪北江全诗文集》。
[6] 《沈氏农书·运阳地法》,见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第69页。
[7]王命岳:《家训》,见《切文斋文钞》卷九,转引自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198页。
[8]民国《续修广饶县志》,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193页。
[9]光绪《代州志》卷三《地理志》,转引自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l期。
[10]嘉庆《密县志》卷十一《风土志》,转引白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l期。
[11]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349页。
[12]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十六《七件事》,第482页。
[13]王永年:《紫频馆诗钞》,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中华书局l963年版,第396~397页。
[14]乾隆《干山志》卷四《荒政》,“乡镇志专辑”,第一册,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594页。
[15]宣统《续修枫泾小志》卷十《拾遗》,“乡镇志专辑”,第二册,上海书店l992年版,第325页。
[16]焦循:《雕菰楼集》卷二《荒年杂诗》,道光四年(1824)刊本,第la一2a页。
[17]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二笔》卷十三《人肉价值》,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0页。
[18]田岂蘅:《留青日札》卷二十六《七件事》,第282—283页。
[19]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349页。
[20]参阅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l999年第l期。
[21] 《沈氏农书·运田地法》,见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第69—70页。
[22]参阅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中国经济史研究》l996年第3期。
[23]谢肇涮:《五杂俎》卷十四《事部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8页。
[24]道光《江阴县志》卷十六《人物·孝弟》,“丛书·华中”,第456号,第四册,第1726页。
[25]甘熙:《白下琐言》卷七,第7a一7b页。
[26]刑课题本署福建抚杨魁,46.9.22,转引自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第177页。
[27] 《沈氏农书·运田地法》,见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增订本),第69页。
[28]同治《会昌县志》,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第1170页。
[29]参阅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l999年第l期。
[30]王鸿泰:《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载《新史学》,第十一卷,第3期,2000年9月,第44—46页。
[31]黄卬:《锡会识小录》拯一《备参上》,“丛书·华中”,第426号,第74~75贞。
[32]光绪《海盐县志》卷八《舆地考·风土》,“丛书·华中”,第20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l974年版,第935页。
[33]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一《娄关小志序》,咸丰九年(1859)刊本,第41a页。
[34]道光《璜泾志稿》卷一《风俗》,“乡镇志专辑”,第九册,第131页。
[35]光绪《海盐县志》卷八《舆地考·风土》,第9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