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家庭收支概况——《中国家庭史》第四卷第三章第二节
三、收支概况
那么当时一般家庭收支状况究竟如何呢?限于资料、篇幅和时间,我们只能在此就个别的点略作说明。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当时人口的主体无疑是农民,农民又以自耕农和佃农为主。从明到清,随着人口的不断膨胀,总体上,全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呈日趋减少之势。不过,由于新生产技术、新作物的引入,特别是农户单位面积土地中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以及多种经营和家庭手工业普遍开展,普通农户的收益实际上可能还有所增长。据李伯重的估计,清代中期江南农户的净收入要比明后期多出15%左右[1]。当时,正常情况下,农户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经营和以纺织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当时普通农户的土地耕作规模,各地之问有较大的差异,江南地区大约为10亩,而湖广、四川在10~30亩之间,华北约在30亩上下,而山陕则多在四五十亩左右[2]。当然,由于各地亩产量与经营效率等的差异,家庭收入与土地经营规模并不成正比,土地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江南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反而要优于其他地区。因受资料等条件的限制,我们的说明主要以江南地区为例。
据方行的研究,在浙西等稻桑耕作区,以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来计算,户耕10亩,其中7亩种田,3亩种桑,在清前中期,可收益米21石,治桑养蚕约可获丝20斤,约值银24两。而在苏南等稻棉作业区,普通农户稻田数一般在5亩左右,可收获米15石,另外农户种棉纺织可得棉布80匹,可值钱21.6钱,约相当于银30两。[3]而支出,治田10亩,生产成本,约为一家五口口粮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口粮支出大体为18石,则为米6石,当时的米价基本在每石1两上下浮动,以1两计,则需银6两。另外,为生活支出,口粮18石,副食7两,居屋约1.6两,衣服3两,燃料3两。总数为米18石,银14.6两,石米以1两计,则为32.6两。[4]在方氏的计算中,居屋一项是以租房者论的,实际上,就普通家庭的日常开销而言,这一项应该可以省去,但土地显然还需负担国家的赋税,当时平均每亩的赋税负担各省有很大的差异,其中以江浙两省最重,按乾隆十八年(1753)计算(此后变化不大),江苏每亩银4.9分,粮3.13升,浙江6.1分,粮2.46升。[5]这样,10亩地,在江苏共需负担银0.49两,粮0.313石;在浙江则银0.61两,粮0.246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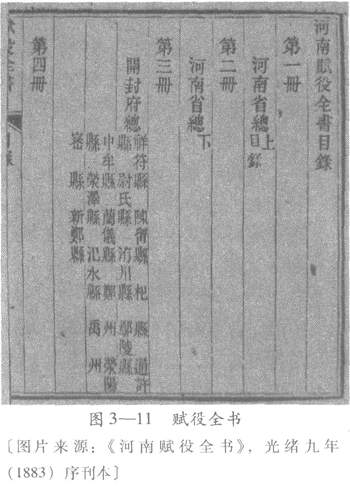
按石米1两计,则江苏需银约0.8两,而浙江约0.9两。浙西,一年的收入约45两,支出37.9两;苏南,收入也约为45两,而支出37.8两。收支相抵,分别余7.1和7.2两。而且,在上述的开支中,副食一项,固然可以计算价值,但实际上,在农家,利用田间地头基本就可以自足,除了盐、油等项外,泰半不需现金开销,若将这项开支减去三分之一,则剩余部分则可达到11.8和11.9两。当然,这只是最基本的开支,此外,像文化娱乐、逢年过节等,也会有一定的支出。不过,如果是一个拥有10亩地的自耕农,只要辛勤劳作,勤俭持家,正常年景,足以保持收支平衡,而且还可以保证一定的积蓄,以备建房、葬亲娶媳等长远开销。但若是佃农,不必交税粮,但需纳租,清中期江南常年的地租基本在每商1石左右[6],则需纳租10石,即银10两,积余只剩2.7两。因此,作为佃农,若不降低生活水准,更精打细算,或更加勤奋租种更多的土地,生活就会显得相当拮据,而且家庭经济也会非常脆弱,很难经得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以上分析的只是农民,还有士以及工商,他们的收入,作为士绅和商人,富者收入来源广大,显然难以计算,但当时一般的士人和商贩,生活也并不见得十分宽裕。正如洪亮吉所说:
四民之中,各有生计,农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贾各以其赢以易食者也,士亦挟其长,佣书授徒以易食者也。除农本计不议外,工商贾所入之至少者,日可余百钱,士佣书授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钱。是士工商一岁之所入不下四十千。[7]
按洪亮吉粗略的估计,普通士工商一人所入约四十千钱,洪的写作时间是乾隆后期,当时的银钱比价约为每两900~1000钱。故折合成银子为40~45两。与上述一个农民家庭的收入类似。不过要看到,这里说的是净收入,而且也未包括家庭其他成员的劳动所入。因此,总体上,他们比农家的生活应该会稍稍宽裕一些。
由此可见,当时一般家庭,正常年景下,虽然生活不够优裕,但若能做到勤俭节约,应该可以保持收支平衡并有所积余,也应该有能力应付那些维持一个家庭正常维续的长期投资。但当时社会上存在着相当多没有土地,甚至无法租到必要数量的土地的农民,由于社会并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即使有机会佣工,生活仍会相当艰难[8],所以当时社会的贫困人口也是大量存在的。一旦遇上严重的灾荒,情形会相当悲惨。不少文人的记录使我们能够略知灾荒之年的种种凄凉惨烈,比如:
(雍正)十一年春,(太仓州镇洋县璜泾)民大饥,尽粥其所有,则毁屋,又不足,则鬻子女,时无余钱买力给者不克鬻(原文如此——引者),民饥不可忍,乃刈豆及麦,熟其叶而食之。尽皇皇然多无地着心,弃其子女于道而流,强不可弃者,泣而投之河,哀鸣满道。村落或有树榆者,争解其皮,皆一聚而白。流民道瑾,积尸满野,日色曝之,浮臭郁蒸,行者为之不通。饿人以夜走他境,腹乏不充,秽气入之,暗中足触僵尸,一蹶不能振起,积日愈多。[9]
这还是在江南,在其他地方,更是如此。比如晚清光绪初年,由于连年奇旱,造成罕见“丁戊奇荒”。大灾蔓延整个北方地区,并且波及南方一些省份,造成至少一千万人的死亡。以致当时清朝官员每称之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来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由于长时间大面积的减产与绝收,民间储藏已经匮乏,在春季之时,灾民尚可以草根、树皮果腹,入夏之后,草根既无,树皮也尽,于是灾民无以为食,倒毙于途者,在在皆是。为了维持一线生机,灾民取小石子磨面为食,或者挖观音土以充饥,然而不数口即腹胀而死。有的则将柿树皮、柳树皮、果树皮、麦糠、麦秆、谷草等等和着“死人之骨、骡马等骨碾细食之”,至于家犬鸡猫牛羊等牲畜早已宰杀殆尽,有的干脆“将牛羊等皮扯块连皮毛掷灶中,火燎毛尽,皮可半熟,不待烹调,不嫌臊臭,两手一搓,忙催入口”。[10]一切可食之物食尽之后,竟发生了人吃人的人间悲剧。
死者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脔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竞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11]
春夏之际,雨水较为充足,本可缓解旱情,但瘟疫却席卷而来。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山西省因瘟疫而死者,十有二三。临汾县县令组织各地绅董,掩埋尸体两月,尚未掩埋干净。平阳府东门挖掘万人人坑三五十处。秋凉之时,黄沙白草,累累白骨,不见炊烟,杳无人迹,真乃人间地狱[12]。
注释:
[1]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311页。
[2]参阅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下),第2066~2075页;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241~268页。
[3]参阅方行:《清代农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形式》,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l期。
[4]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中国经济史研究》l996年第3期。
[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l980年版,第394页。
[6]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下),第l750页。
[7]洪亮吉:《卷施阁甲集》卷一,第6b—7a页,《洪北江全诗文集》,四部丛刊本。
[8]关于佣工生活的艰难,可参阅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下),第l875~1877页。
[9]乾隆《璜泾志略·灾祥》,“乡镇志专辑”,第九册,第257页。
[10]《万国公报》,第八册,第5114页;《申报》l878年3月29日,转引自李文海、程献、刘仰东、夏明方:《中国近代卜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11]《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第514—515页。
[12]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第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