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家庭收支概况——《中国家庭史》第四卷第三章第二节
要细致地讨论明清时期家庭的收支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各个家庭经济状况千差万别,且不论资料是否允许,即便有足够资料,我们也无法在有限的篇幅中对_丁^差万别的情况作出一个完整的说明。当然,若有完整的数据,就平均值作一计算和说明,倒是简便可行,但在历史上,毫无疑问,不可能找到这样的数据。所以,这里只能就各个阶层人们的收入和支出作一概要的说明,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某些典型家庭的收支作一计算。
一、收入
当时的各个社会阶层不同的家庭收入来源虽然各种各样,但大体上应基本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俸饷及特权收入,这类收入主要出现在官僚、吏员以及士兵等家庭中,他们特别是其中的官员,由于手巾都握有特权,利用特权获取的收益一般会远远超过明确俸饷收入[1]。
二是土地和农业收入。作为一个农业社会,这应该是当时国家和大多数人最主要的收入。其主要包括土地出租的租税收入、雇工经营土地的收入、自耕农耕作土地的收入、佃农佃种土地的收入以及雇工从事农业劳动的收入。农业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产业,明清时期的农业生产与前代相比,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作物的口趋多样化以及劳动力投入不断增多等原因,农业的整体收入和单位面积收入均有较大提高[2]。
三是工商服务业收入。明清时期,特别是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工商业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举办工商业固然可以获取较大的利润,同时还可以吸收社会上大量的待业人口,增加从业人口的家庭收入。比如,在《金瓶梅》中,我们看到,西门庆一家的收入基本依靠商业,他家的商业经营不仅让他们一家过着富裕骄奢的生活,而且也让其手下的一些伙计收入不菲。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当时的工商业活动相当繁盛,比如在清代的苏州:

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省青兰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踹砑光。即有一种之人,名日包头,备置菱角式样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屋、家俱之费。习此匠业者,非精壮而强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县之人,递相传授,牵引而来,率多单身乌合不守本分之辈.……从前各坊不过七八千人,……现在细查苏州阊门外一带,充包头者共有三百四十余人,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匠各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百余块,人数称是。[3]
同时,随着工商业活动的频繁以及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社会服务业也日渐繁荣。这一产业的发展,显然可以使当时众多所谓城市的“无业游民”获得更多的收入。对此,嘉庆、道光时期无锡的钱泳曾就江苏主要是苏州的情况指出:
昔陈文恭公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金、阊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昔苏子瞻治杭,以工代赈,今则以风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4]

除了一般的服务业,当时日常生活的中介服务也是一些人获得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比如,在各种买卖契约中充当中人,收取一定的中介费[5]。又如,媒妁之言乃婚姻当时成立的必需条件,所以,职业的和半职业的媒婆群体在明清时期也颇为活跃,作为三姑六婆[6]中的一员,媒婆尽管在当时的小说等文献中,多以负面的形象出现,但从中不难看出,她们借此获取的利益并不少。比如,《金瓶梅》中,在西门庆死后,春梅和潘金莲因为与陈敬济的奸情被月娘发觉,先后被逐出家门,让原来做中的薛嫂和王婆分别领去嫁卖。结果,她们两人分别从中赚取了三十七两五钱和八十两的差价。[7]关于春梅的嫁卖,书中描写道:
周守备见了春梅,生得模样儿比旧时越又红又白,身段儿不短不长,一对小脚儿,满心欢喜,就兑出五十两一锭元宝来。这薛嫂儿拿来家,凿下十三两银子,往西门庆家交与月娘。另外又拿出一两来说:“是周爷赏我的喜钱,你老人家这边不与我些JL?”那吴月娘免不过,只得又秤出五钱银子与他,恰好他还禁了三十七两五钱银子。十个九个媒人,都是如此赚钱养家。[8]
当然,在普通家庭问保媒,不可能有如此高的赚头,但民间,作为中介费的媒钱基本都在财礼钱的10%[9],比例要超过田产、房屋等买卖的契费。

四是接受国家或社会的救济以及亲友馈赠的收入。每当发生灾患,明清国家一般都会采取一些救济措施,比如在清代规定,受灾五分以上为成灾,若勘成灾,灾民分极次贫可享受一到四个月的口粮赈济。赈济标准为每日大口授米五合,小口(十六岁以下)半之。若米谷不足,则按时价折钱。此外,受灾五分以上(包括五分)的田地还可蠲免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七的赋税[10]。而且这些规定也并非一纸具文,例如,在被一般认为已经走向衰败的道光时期,仍可以看到这类救济的切实执行,不仅国家调拨帑金,而且还积极发动民间社会力量开展救济活动。比如,道光三年(1823)南方普遍大水,江南地区受灾尤甚,在江苏,国家共调拨帑银170余万两,并筹集民间捐款195万两。而在苏州一地,官赈和社会捐赈分别为35万两和50万两以上,基本实现了“民沾实惠”、“一境帖然”[11]。除了灾荒救济以外,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中后期以来,社会上还兴起了众多的Et常社会机构和宗族义庄,无疑也会让一些下层民众获得一些收益[12]。当然接受救济基本都是社会的下层贫民。而亲友之间的馈赠,则是社会所有阶层共有的现象,虽然亲友间礼物的流动总体上是平衡的,不过对某个家庭来说,在某一特定时间内,这类馈赠亦可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此外,对那些赤贫家庭来说,鬻妻卖女也会成为其摆脱困难的手段。特别是在灾荒之年,鬻卖儿女,为人作奴婢或者小妾,更是十分流行,价格之低廉,甚至斗米即可买一人,千钱即可买一仆。有一首诗描绘了被鬻卖之女儿的凄凉心境。
有女有女来大梁,驱车驱车转他乡。飞絮一随不知处,杨柳不集双鸳鸯。一顾远兄弟,再顾别爷娘。眼枯忽作溺人笑,天涯海角长相望。[13]

值得指出的是,明清时期,妇女在家庭生计中,已逐渐开始承担起较为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一时期妇女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自民国以来,已有不少的论述[14]。这些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妇女为改善或维持家庭生计所开展的经济活动范围相当广泛,比如农业生产、纺织、佣工补贴家用乃至从事中介服务等某些商业活动,而且其地位和作用日渐重要。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蚕桑业和棉纺织业的日趋发达,更使妇女独立维持生计成为可能。据李伯重估计,一个农妇从事纺织作业,若一年纺织200日,其收入可以维持1.5人的饭食,如果其劳动日延长到265日和360日,则可维持饭食的人数也相应增加到2人和2.8人[15]。这表明,当时一个勤奋能干的妇女独立维持生计乃至养活一个子女是可能的。这一点,在当时的文献中很容易得到验证。比如:
闽吴某居上新河,本宦家子,幼失怙恃,家道中落,贫无以自存。母素有一婢,极贤淑,以主家沦丧,藐然一孤,誓志不他适,独肩抚育之任。赁敝屋数椽,衣食之资,惟十指是赖。[16]
盛支燧,字恂如,幼孤,母陆苦鞠之。贫不能从师,乃助母昼夜纺绩以易米。母子依倚二十余年,虽困甚不受人周恤[17]。
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18]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妇女由于勤奋和善于经营而使家庭小康的例证,尽管这并不常见。比如,乾隆十四年(1749),山东莘县发生的一件命案中,因债务纠纷被杀的赵王氏就是这样一位妇女,据她的弟弟供述:
这死的王氏是小的姐姐。小的姐夫赵金,因家里穷,往口北去了,多年没有回来。家中只有姐姐合甥女臻姐过日子。姐姐纺花织布,积了些银钱,当买了几十多亩地,又放些钱帐[19]。
又如,“沈有斐妻潘氏,年二十四夫亡,尤子,昼夜纺织,历数年积赀置田,以从子为嗣。”[20]不仅如此,根据高彦颐的研究,明末清初,还出现了一些像黄媛介、王端淑等饱读诗书的知识女性外出笔耕为业,而丈夫反而在家充任“内人”角色的现象[21]。这种现象固然不甚普遍,但在文献中也不难发现,比如,清中后期上海的钱氏:
钱氏,名韫素,字定娴,闵行李尚嶂妻。……尚嶂幕游数载始一归省,无内顾忧。……赭寇乱后,尚暲家居著书,境益困,氏应诸宦族延聘,课徒十余年,藉束倚以资补助,自奉至啬,而周恤贫乏不少吝。[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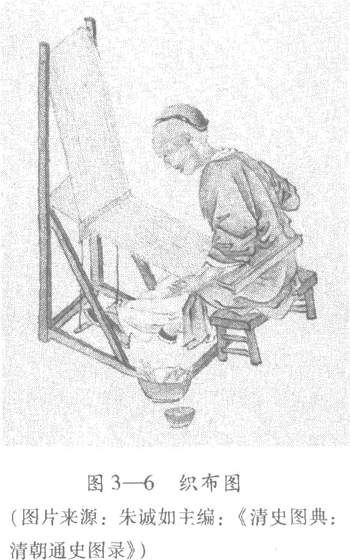

不过,我们也不宜就此过高地估计当时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冯尔康曾在述论了妇女在劳动中的重要角色后,指出:
女子干活很多,很辛苦;农忙时务农,勉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农闲时日夜纺织;还有笨重的、琐细的家务劳动。她们的辛勤劳苦,已为当时人所指出:“村妇之劳,甚于男子”。但妇女的家务劳动,是为家庭,为丈夫服务,不是社会性生产劳动,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她们作为男子助手参加的一些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其家庭经济收入中不占重要比重。所以不掌握生产手段的妇女,没有独立的经济,生活上必须依靠男子,这就决定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被支配地位。[23]
冯尔康虽然没有就此进一步举证并展开论述,但笔者以为,他这一总体上的估计是符合事实的。那些绅富之家自不必说,就是在普通人家的女子,就全国的情况看,也仍基本出于依附地位,这一点,从当时大量的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比如:
陕西干州王江供:四十岁,女人王氏,有一子。小的佣工度日,去年得了痞病,做不得活,穷苦难过,女人儿子时常受饿。[24]
安徽怀宁县金黄氏供:六十一岁,丈夫已死,生两子。长子金陇友,娶媳冯氏,只生一孙女(十二岁)。次子金苍友,他弟兄们已分居,轮流供膳。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长子死,媳冯氏守节,针工度日,近闻针工稀少,次子肩挑艰难,只能供养小妇人一人。冯氏母女时受饿。[25]

实际上,文献中那些独立维持生计的女性都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无奈之举,而且,除了个别的情况外,一般也举日维艰。比如前举盛支燧的例子,又如:
严斗林,三岁丧父,母朱苦志纺织,斗林拾薪以养。十一岁,母病瘫痪,斗林无可为计,乃求乞得食,辄驰归拳母。[26]
一般情况下,妇女往往会为琐碎而繁杂的家务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27],即使在江南地区,妇女在日常劳作的以外时问纺织,也常常只是被视为对家庭生计的补充。比如,清代上海的王蔼言曾在一首诗中写道:
织布女,首如飞蓬面如土。轧轧千声梭若飞,手快心悲泪流雨。农忙佐夫力田际,农暇机中织作苦。贫家习苦自忘疲,积得余资期小补。[28]
而且就是那些外出谋生的妇女在观念上仍将“内人”视为自己的本分,像前面谈到的上海的钱氏,虽然家里依靠她维持生计,但仍只是说“藉束惰以资补助”。高彦颐在讨论妇女的“谋生游”时也认为,“这种夫妻倒置的位份,反映了明清之际妇女诗文的商业价值,然社会上‘男主外女主内’的基本性别分工并未因而丝毫动摇”。“黄媛介虽代夫营生,因而享有其他闺秀无从涉足的行动空问与交际自由,却无意质疑古有的三从四德规模。‘声影不出衡门’的自辩,反证媛介对于这种规范起码在门头上和字面上的服膺。”[29]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妇女的劳动在家庭经济收入中的作用大大增强,但总体上,她们作为男子助手参加的一些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其家庭经济收入中不占重要比重。“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仍是最基本的。
注释:
[1]官员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小吏,甚至被视为贱民的皂隶,利用官府权势,在应承差役时,也不难上下其手,谋取利益。对于官吏这类勾当,方苞在《狱中杂记》有生动描写:
而十四刊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史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拘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习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 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 外,使其党人索财务,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支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惟人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勾者十四三,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训者三人,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问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方苞:《王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六《狱中杂记》,四部丛刊本。)
甚至士兵,在遇兵事时,同样可以鱼肉百姓。比如,顺治十六年,拨发水师镇守上海,“有二都司、四千总、八把总,城中略可房宅,尽被占去。十家供养一兵,兵丁之可恶特甚,而莫敢声言。盘放营债,民受茶毒者不独城内,村中破家者更多。甚有淫妇,大张明著与彼往来;又有贪其利,将如花似玉之女,与彼结亲;又有将男女卖彼为奴婢;又有非亲非故,任其出入房户,一家妇女无分老幼与之淫媾,种种可恶,罄竹难书。”(姚廷遴:《历年纪》下,载《清代日记汇抄》,第97页。)
[2]参阅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406页;方行、经君健、魏金玉士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l945~2174页。
[3]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3页,转引自冯尔康:《卜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江南商品经济中的几个问题》,载《清史沦丛》第七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4]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安顿穷人》,第26页。
[5]比如,在浙江丽水,“房屋买卖要付给牙郎及代笔一定的手续费,叫做‘契费’,习惯有‘房五地四田三’的标准,房五即以房价的百分之五作契费,由双方付出,给牙郎及代笔共分”。(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l986年版,第555页。)
[6]关于三姑六婆,可参阅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
[7]齐烟.汝梅点校:《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八十六、八十七回,第1226、1244页。
[8]齐烟.汝梅点校:《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八十六、八十七回,第1226、1244页。
[9]参阅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第l69~172页。
[10]参阅李向军:《清代救灾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71—74页;杨景仁辑:《筹济篇》卷首《蠲免功令》,光绪四年(1878)重刊本。
[11]参阅余新忠:《道光三年苏州大水及各方之救济——道光时期国家、官府和社会的一个侧面》,载张围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占籍出版社l999年版。
[12]关于日常的社会救济机构,可参阅[日]大马造:《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日本)同朋社l997年版;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l997年版。
[13] 《申报》第十四册,第374页,光绪四年(1878)闰.三月初一日。
[14]民困时期徐珂撰辑的《清稗类钞》,虽然是一部资料汇编,但关于妇女在社会劳动中的地位,他其实已通过多种资料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比如,以下言论显然具有一定研究性,“常言男耕女织,又言夫耕妇馈,似种植之事非妇女所与闻,则是未尝巡行阡陌考察农事之故也”(《清稗类钞·农商类》,第五册,第2256页)。“我国妇女,向以徒手坐食为世诟病,其实此富贵之家耳,若普通人家,则有职业者为多。”(《清稗类钞·风俗类》,第五册,第2211页)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作者对那种认为妇女不参加劳动的意见的批评。现代的研究,冯尔康较早结合妇女的缠足考察了清代妇女在农业和纺织业中的劳动情况(《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载《清史研究集》第五集)。王仲论述了明清江南妇女在养蚕丝织、棉纺织和田间劳动中的角色与地位,认为江南妇女的辛勤劳动使自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都有一定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劳动中妇女的角色、地位》,载《中国农史》l995年第4期)。李伯重从“男耕女织”这一家庭男女合作的模式出发,较为理论化地探讨了江南地区从明代的“男女并耕”模式到清代的“男耕女织”模式的转变过程,并对“男耕女织”模式的合理性给予高度评价(《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9~314页)。陈瑛珣主要利用契约文书揭示了明清时期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它们包括农业劳动、纺织、佣工、做中人与媒证以及放款生息等商业活动等(陈瑛珣:《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妇女经济活动》,台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47—317页)。
[15]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302~303页。
[16]甘熙:《白下琐言》卷七,第7a页。
[17]光绪《嘉兴府志》卷五十三《秀水孝义》,“从书·华中”,第53号,第三册,第1445页。
[18]尹会一:《敬陈农桑四议疏》,见贺长龄等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八。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l44页。
[20]光绪《奉贤县志》卷十四《列女志·节孝》,“丛书·华中”,第l5号,第三册,第778页。
[21]参阅高彦颐:《“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期,第41~47页。
[22]民国《上海县志》卷二十五《列女传》,“丛书·华中”,第l4号,第四册,第1545—1546页。
[23]冯尔康:《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载《清史研究集》第五集。
[24]刑课题本陕西巡抚秦承恩,55·7·12,转引自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第33页。
[25]刑课题本大学士阿桂等,嘉庆元年·6·24,转引白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第232—233页。
[26]道光《江阴县志》卷十六《人物·孝弟》,“丛书·华中”,第456号,第四册。第1726页。
[27]上海地区的一首民谣《十忙歌》充分表现了妇女家务的辛劳:“一忙忙,青铜镜子照梳妆。二忙忙,早起开门地扫光。三忙忙,婆婆房里送茶汤。四忙忙,满床儿女着衣裳。五忙忙,柴米油盐管厨房。六忙忙,丈夫出门抈衣裳。七忙忙,端正男儿进学堂。八忙忙,姑娘小叔汰衣裳。九忙忙,男长女大配成双。十忙忙,交代门头后辈当。此《十忙歌》,言妇女勤操内政,尤空闲一刻也。”(胡祖德著:《沪谚外编》卷上,第28页)现代作家苏雪林也以细腻的笔调述说了妇女承担家务的辛劳而“无功”。她说:“我以为生活本应该夫妇合力维持的,可是男人每每很巧妙地逃避了,只留下女人去抵挡。虽说男人赚钱养家,不容易,也很辛苦,但他究竟不肯和生活直接斗争,他总在第二线。只有女人才是生活勇敢的战士,她们是日日不断面对面同生活搏斗的。每晨一条围裙向腰身一束,就是披好甲胄,踏上战场的开始。不要以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微不足道,它就碎割了我们女人全部生命,吞蚀了我们女人的青春,美貌和快乐。女人为什么比男人易于衰老,其缘故在此。女人为什么比男人琐碎,凡俗,比男人显得更斤斤计较,比男人显得更实际主义,其缘故亦在此。”(苏雪林:《苏雪林选集·家》,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转引自陈瑛珣:《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妇女经济活动》,台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15页)
[28]道光《塘弯乡九十一图里志·物俗》,“乡镇志专辑”,第一册,第195页。
[29]高彦颐:《“空间”与“家”——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3期,第45、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