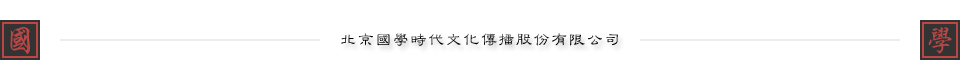【清代】冶铁、铸铁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五章第一节
二 清代冶铁业的发展
清代采铁、冶铁的生产技术没有什么改进。在采矿上,仍是传统的锤、凿开挖,明代所述火爆法,反而未见记载。在冶炼方面,炼焦的使用,也反而未见记载。尤其是炼铁炉的构造,并未见进步。
表5-1清代各种矿在采厂数
| 年代 | 合计 | 铜 | 铅 | 铁 | 金 | 银 | 银铜铅 | 锡 | 水银 | 煤 | 硝 | 硫璜 | 雄黄 |
| 康熙元年1662康熙二十年1682
康熙三十七年1698 康熙四十七年1708 康熙五十七年1718 雍正六年1728 乾隆三年1738 乾隆十三年1748 乾隆二十三年1758 乾隆三十三年1768 乾隆四十三年1778 乾隆五十三年1788 嘉庆三年1798 嘉庆十三年1808 嘉庆二十三年1818 道光八年1828 道光十八年1838 年代未详 |
511
28 56 68 105 152 215 262 282 311 307 283 302 296 290 279 80 |
1
2 16 16 30 35 44 58 61 55 56 57 52 50 51 52 6 |
1
6 10 11 25 28 36 40 39 31 24 18 20 19 3 |
17 17 17 24 54 69 91 90 92 84 82 112 127 121 112 59 |
1 3 3 5 5 4 6 6 7 16 11 11 8 7 5
|
15
2 12 17 21 24 32 28 28 24 27 24 29 26 28 30
|
1 6 5 11 12 10 10 8 8 9 4 3 3
|
1 1 2 3 6 9 9 10 8 7 5 5 5 5 6 |
45
5 6 6 4 5 5 8 8 8 6 6 7 7 7 7
|
7 14 17 27 24 19 15 14 17 17
|
2 3 5 2 9 27 27 27 27 26 20 20 5 |
1 1 1 5 5 5 7 10 11 10 10 10 10 8 1 |
2 2 2 1 1 1 1 1 1 1 1
|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经387-389页。原据清代矿课,钱法档案,历朝会典、事例、则例,各省地方志及有关私记载整理。
直到鸦片战争前,清代最先进的炼铁炉,仍是广东明末遗制的瓶型高炉,这种炉的最高产量一昼夜可达3,600斤,我们已作过详细介绍。【38】清中叶新兴的陕西南部铁产区,其“铁炉高一丈七八尺,四面椽木作栅,方形,坚筑土泥,中空。上有洞放烟,下层放炭,中安矿石。矿石几百斤,用炭若干斤,皆有分两,不可增减。旁用风箱,十数人轮流曳之,日夜不断。【39】”这种高炉,看来是明代遵化炉的同一类型,只是加高了5—6尺,与广东高炉相等,但其容积相差远甚。这是因为,方炉只是便于筑造,不能过大,燃烧效果亦差。遵化高炉日产量540斤,陕西高炉以加大三分之一计,不过700斤。其鼓风设备则可能已利用封闭式风箱(明末《天工开物》所记亦系封闭式风箱),但亦因此耗人力甚多。原资料说,一炉所需匠夫共十数人,鼓风即占去十数人。四川也是清代发展起来的铁产区,其所用炼铁炉更属小型。下面将引用其记载,每炉只司炉1人,鼓风2人,日产量仅27斤。
但是,清代产铁的地区扩大了,炼铁炉也增多了,所以铁的生产仍是发展的。我们没有铁产量的统计,由于铁课折银,所知情况反不如明代,不过,从其他一些材料看,清代铁的产量确有增长,但比起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来说,又是落后的;到十九世纪后期,我为已是一个用铁相对贫乏的国家了。
彭泽益同志对清代铁矿的开发有个统计,据他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到道光十八年(1838),全国共报开铁厂280处,期间停闭168处,期末尚在开采的112厂。表5-2是每隔10年在开采厂数的摘要。
表5-2清代矿在采厂数
| 年代 | 合计 | 云南 | 四川 | 广东 | 广西 | 湖南 | 陕西 | 江西 | 其他 |
| 康熙二十四年1685雍正三年1725
雍正十一年1733 乾隆十年1745 乾隆二十年1755 乾隆三十年1765 乾隆四十年1775 乾隆五十一年1786 乾隆六十年1795 嘉庆十一年1806 嘉庆二十年1815 道光三年1823 道光十五年1835 年代未详 |
1718
50 70 93 91 91 86 82 115 116 121 112 59 |
1616
21 21 21 12 12 12 12 12 13 13 14 |
11
1 1 4 13 14 14 14 16 14 16 16 |
1
27 26 41 40 35 29 25 24 25 31 28 45 |
1 2 4 4 3 2 7 7 9 9 14 |
10 10 6 6 6 6 6 8 3 3
|
27 27 27 27 |
4 6 7 8 7 7 7
|
1 11 15 16 16 16 16 15 15 15 8 |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经387-389页。原据清代矿课档案,历朝会典、事例、则例,各省地方志及有关私记载整理。
冶炼的情况,我们也不妨作个粗略的考察。广东是清代冶铁最发达的地区,李龙潜同志有过研究。【40】据他研究,从康熙到道光年间,广东省商人经营的冶铁工场共有高炉85座,分布在三十个县,主要在广州、韶州、惠州、嘉应州四府。都属大型高炉,每炉年纳饷银50-53两,仅个别稍秒,惟不知其各时期停闭和实存数。雍正十二年(1734),广东总督鄂弥达称:”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41】,似乎多了一些,可能是连同交纳饷银的土炉计算在内了。乾隆后期,炉数大减(多是矿尽停闭)。嘉庆四年(1799),有材料说广东共有高炉25座;到道光时,大约20余座,亦有说30座【42】。据嘉庆二年(1797)一个材料,广东高炉每座年产猴80-90万斤。【43】高时按40座计,年产量在3,500万斤左右,低时按25座计,在2,000万斤左右,又清代广东的铁课,高时达714万斤,低时589万斤【44】,按二八抽计,产量高时达3,570万斤,低时2,940万斤。比起明代最高产量,高时亦不过增加25%强,低时反有减少【45】。盖广东铁矿,到清中期已渐枯竭了。
陕西原有铁矿开采,嘉庆以后大兴,成为一个大铁产区。这时铁厂分布在陕南凤县17处,略阳县5处,宁远厅2处,宁陕厅3处,共27处铁厂【46】。其高炉数未详。惟据称,其小厂有炉3-4座,大厂倍之(资料见后文),平均每厂按4座计,约有炉100余座。陕西高炉年产量126.000斤,部计100炉年产共约1,200余万斤。
四川铁冶发展于乾隆年间,也是清代一个重要的铁产区,据称,乾隆十七年(1752),威远县开炉6座;二十六年(1761),屏山开炉4座;二十八年(1763),屏山县再开炉4座;三十一所(1766),宜宾县开炉2座;五十六年(1791),洪雅县开炉2座【47】。又据《通典》,四川铁炉都属小型,如前所述,每炉年产量不过4,800斤,是全省年产不过35万斤。
福建是个老铁产区,延平(尤溪)铁早负盛名,但产量不多,清代转衰。乾隆八年(1743),据沙县,尤溪等八县亲开铁炉共69座,内大炉5座,小炉64座,惟炉式及产量匀未详。【48】
广西是清代新兴的一铁产区。据乾隆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一年(1753-1817)前后11个关于广西矿课的材料,列铁炉数都在50-60座左右,平均数56座分布在约10个县。【49】其炉式则未详。
江西的铁产区主要在长宁、兴国二县。长宁县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报开铁炉4座,五十九年(1794)报一炉4座,嘉庆十七年(1812)报开铁炉1座,共9座【50】。兴国县情况未详。
湖北省于雍正间题准澧州石六、慈利、安福、永定四县铁矿任民开采。乾隆四十六年(1781),石门县派矿课3,000斤,慈利县派矿课5,000斤。【51】按二八抽铁计,产量为40,000斤,依四川式小型炉计,约有铁炉8座。全省又不止此。
云南是个老矿区,铁厂不少,炉数未详。惟云南铁产,乾隆以后是衰退趋势。湖南、山西、安徽者是后起的铁产区,尤其湖南、地拉相当重要,但铁炉和产铁情况,都无资料可寻。
以上,除广东、陕西两个主要铁产区外,其余各省有数可查的铁炉共144座。考虑到未全数字,及湖南、云南、山西、安徽等省,若共有250座炉,并不为多。均按四川小型炉计,每年产量共约120万斤。这样,全国铁产量约在4,7000万斤左右,最多时不到5,000万斤。
三 冶铁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清代冶铁仍然缺乏比较广泛的资料,我们还只能从一些事例中来观察生产关系。
湖南:“辰〔溪〕邑矿厂情形,其挖,开设炉墩于县属溪边河岸,雇募人夫,煽铸生铁,名生板者,有乡厂、容厂之分。乡厂者,数人共一炉墩,各以所获炭、矿,轮流煽铸,为日甚暂。客人者,或一人或数人合伙,先期收买炭、矿,每秋凉时开炉,至次年春夏之交为止。所出生板,俱装运浦市,出售于砂铁厂。……属内开设炉墩之处,原无定在,故未载明。”
“辰邑山多田少,无田可耕之贫民,所在多有。当农忙时为人雇工,犹可自食其力;及至秋后无他艺业,往往于产有铁矿处所,竭力开采,以此获得值自瞻。计阖县挖矿营生之人,动以数千。开采得矿,矿贩于此收买,装运近河开设炉墩之处。又有厂民收买炭、矿,雇募,煽铸生板。计每炉一座,所需工及挑运脚夫,约数十人,十座则数百人矣。邑属以此食力养家,亦以千计。其烧炭之炭户,装矿之船户,取给于此者,亦数百家。”【52】
从这段记载看得很清楚:采矿、烧炭的都是小生产者,他们大都是无地农民,农忙时为人帮工,秋冬采矿、烧炭。他们所采矿砂,由矿贩收买,装运卖给“生板”,即开炉冶铁之人。冶铁需大量的水,故都在溪边岸。这里的炼铁炉十分简陋,故称炉墩,炼几炉后即须重建,迁徙无定址。“生板”有乡厂、客厂两种。乡厂是采矿农民联合所建,属合作性制裁,建成后,轮流使用,每人用几天,这种情况很普遍,以后在放业中我们常看见以“日”作股份或分配单位,大盖即源于此。客厂是一人或数人合伙,须有一定投资,先期收买炭、矿,供一季度炼铁之用(炼铁季节大体是阴天国十月至次年四月共180天)。这些人可能是地主、富户,更可能是外地来的商人,故称客厂。一个炉需雇工数十人,主要是挑水、运料的脚夫,以及看炉、煽风的工匠。那种小生产者合作性制质的乡厂,轮流冶炼自己所采矿砂,即使雇些人帮忙,也不能算是资本主义萌芽。至于客厂,那就要看厂主身份和雇工条件了,记载不详,难予定论。一般说,这种流动性、季节性的矿产品加工,也和某些农产品加工差不多,可作为商人支配生产的一种形式。
我们所以不厌其详地介绍这段史料,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采矿、烧炭的是小生产者,他们与炉厂主人并无直接关系。即使其产品是由炉厂直接收买,也并非雇工。乃至他们是受炉厂季托或承揽任务,进山采矿、烧炭,计件或计工受值,那也与炉厂直接雇佣的冶工人不同。这在研究矿冶史料时,是应予注意的。
四川威远县:”大山岭、铁炉沟二处,铁矿颇旺,共设高炉六座。每炉一容,用夫九名,每日每户挖矿十斤,煎得生铁厂斤。……计每年〔生产〕六个月,共一百八十日。高记六座,通共用夫五十四名,……共煎生铁二万九千一百六十斤。”
四川屏山县:”李村、凤村、石堰三乡设炉四座,……又于荣丁、利店、茨藜三乡设炉四座,……共设炉八座。每炉采矿砂丁九名,炉夫一名,厢煽夫二名,共计夫丁九十六名,除承值炉厢夫二十四名不能采矿外,实得砂丁七十二名。每丁的获矿砂十斤,每日可获矿砂七百二十斤。每砂十斤,煎获生铁三斤,每日共煎生铁二百一十六斤。”【53】
显然,这两个材料并不是矿厂调查,而是用一炉9名砂丁的平均数来计算生铁产量,以便规定矿课。但它也透露了一些生产关系的情况。第一全是乾隆十七年(1752)的报告,4座炉分设两处,看来是一个炉主。第二例书明,李村等4炉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建,荣西等4炉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建,8座炉分设在6个乡,看来是有几个炉主。这些炉主的身份不详,不过其投资是不大的。用工情况,每记须冶炼工3人,采矿夫9人,这大约是平均数。未提烧炭夫,炭可能是向小生产者买来,也可能是因与计算产量无关,故略。若是,则矿砂亦可能是向小生产者买来,采矿夫9名是否炉主雇用,也还不能肯定,文中说“用夫”,无雇募字样。材料并讲明,它们的生产都是冬春二季180天。这种类型的炉主,是属于小业主,已具有资本家身分,主要看他有几个炉,雇工多少。从这些资料看,还不能肯定。
现在再来看陕西的情况。
“陕西南山铁厂,令商民自出资本,募工开挖。由地方官查明该有商人姓名藉贯,取具日结,加具印结,详明藩司,发给执照,方准开采。……”
“各厂匠役,现状民商人造具循环薄,按名注明年岁藉贯,及上工日期。如有辞工另募,随时添注。于每季底,送该管官稽核。……”
“所出铁觔,只准铸造锅、铁盆、农具,倘有卖给匪徒私制军器等弊,立即严拿治罪。【54】”
“铁山分红山、黑山。黑山为炭窑,……红山则山之出铁矿者,……”
“每炉匠人一名,辨火候,别铁色成分。通计匠、佣工每十数人可给一炉。其用人最多,则黑山之运木窑,红山开石挖运矿。炭路(矿)之远近不等,供给一炉所用之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
“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厂,作农器。匠作搬运之人,又必千数百人。故铁炉川等稍大厂分,常川有二三千人,小厂分三四炉,亦必有千数百人。”【55】
这里,把炉厂的开业、雇工、管理、产品销售等都讲得很清楚。从雇佣劳动看,作者是把劳动者分为匠作、佣工两类。匠是指辨火候的炉匠,须有技术经验,每炉只需一人。佣工是指煽风箱和场内运料的,一炉需十数人。但是,需人最多的是场外的采矿工,、烧炭工,称为夫,供一炉之用,需百数十人。同时,这里是炉厂制,【56】一个大炉厂有炉6—7座,看样子是属于一个资本(独资或许合伙)。这样的炉厂所需劳动,就有二、三千人了。其中,即使是场外的采矿、烧炭工是采取计件给值办法,即买卖关系,单就场内雇工而论,也算得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了。
关于陕西的铁厂,还可补充这样一些情况。其一,空虚地区的冶铁业是在乾隆以来外省流亡农民大批入山开垦,嘉庆初立厅置县对他们采取安置办法的时候,发展起来的。这些人与当地封建关系本来甚少,严如熤《铁厂咏》中说:“一厂指屡千,人皆不耕食。蚩蚩无业氓,力作饱朝饎”【57】,反映他们具有了无产者的性质。不过,失是季节性生产,铁厂工人,尤其是那些采矿、烧柴工人,恐怕不会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其二,在明代就出现了资本巨大的陕西商人。清代陕南山区开发后,他们也经营这里的物产运销,商人投资铁厂,处意中事。”铁厂、板厂、纸厂、耳菌厂皆厚资商人出本,交给厂头雇募匠作”。【58】这些情况,我们在每四章第七节关于陕南木厢业的考察中,已为详述。
最后,广东的冶铁业,在明末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中已予详述。到清代,又有了发展。如前所说,截至道光年间,广东先后开有炼铁炉85座。它们大都是按照当地额定的饷银(铁课)数,招商承办的。
“〔嘉应州〕本州额〔定〕溢铁炉六座。商人卜绍基,在松口堡潭头角承开复兴炉一座;商人王长兴、商伙李世业,在松源堡分煽葵坑、坟承开玉浆炉一座;商人李鸿逵,在磜下堡承开员漂炉一座;商人张际盛,在瑶上堡承开广兴炉一座;又溢炉商李鸿纶,在石坑堡螺子塘承开永源炉一座;商人黄鼎丰,在四督保承开金坑炉一座;递年各认纳银五十两。……至各炉年用矿砂,系在本州松源堡宝坑、石坑宝铁山嶂两处地方产矿山场采运,供炉煽铸。【59】”
这段史料显示,承办冶铁的都是商人,有的原是经营筑造炼铁炉(溢炉)的商人,有的是商人合伙(王长兴和李世业)。不过,每个商人只经营一炉(广东其他州县材料也大都是这样),与前述的炉厂制不同。大约因为广东高炉物大,筑造工精,寿命也长,至少可在炼铁季节连续作用。每炉都有命名,如复兴炉、玉浆炉长(别处还有太平炉等),看来也就是这家炼厂的名称,同时也反映其固定设备投资产不小的,嘉应州产铁矿砂之地只有两处,而炼炉则分布于六个堡,这是因为炼铁须靠近山林和水源,宁可运送矿砂。这也反映其生产规模较大,不能象前引湖南材料那样随便迁徙了。
据雍正十二年(1734)广东总督鄂弥达说:“粤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这可能是连小型的土炉也计算晨内了。雍正十三年,他又说:”各州县〔铁炉〕……佣工受值多,……且穷民入山佣工”。【60】从明末《广东新语》等一些材料估计,大约一炉城冶炼工人60-70人,采矿、烧炭即”入山”者150-180人,尚需牛、船等运输工100人左右。这样其中水陆运输乃至采矿,烧炭诸工,不一定都是由冶炉主人直接雇用,但这并不妨碍冶铁业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