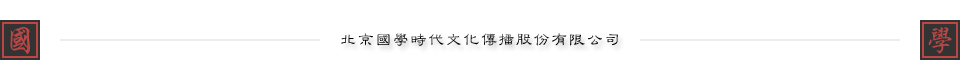《中国土地制度史讲稿》导论
第三节 中国社会经济史料的概况
在这里,准备先来一个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的鸟瞰和总评。
中国的历史是悠久的。中国的史料是丰富的。连周边一些国家的历史年月情节,都要依靠中国史料的著录。我们习惯说,我们的史料是“汗牛充栋”。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假如提到新的科学水平上来要求,那就还存在着若干问题。因为像清朝学者那样片面地求博、猎奇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要求的,是足够说明问题。当前的史料,距离足够说明问题,还相当有距离。因为旧史家多注重人物的活动,特别是帝王将相的生活琐节,他们倒是搜集了不少,这对社会经济有多少说明性呢。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记载了西汉末年一百零几个郡国中人口数字的一笔大略账,且不管它的精确程度如何,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在《食货志》里,他大体说些粗枝大叶的话头,像“见税什五”、“二十倍于古”、“三十倍于古”,以及“巨万”、“亿万计”等等,这仅仅是些大约数。有的还出错误纠缠。如同一篇《(北)魏书·食货志》里,在表述户赋数额时,前文曰户出“粟二十石”,后文曰户出“粟二石”,这就有十倍的出入。害得各位先生各为之说,一说“二石”遗一“十”字,一说“二十石”“十”为衍字,等等,幸亏唐长孺先生又出来调处,说均田令前多大户,故征二十石;均田令后按一夫一妇计。故征二石。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产生如下的想法:像马克思在伦敦的博物馆里,像列宁在莫斯科、彼得堡、苏黎世、日内瓦的图书馆里所遇到的那些分量庞大、数字繁多的调查统计材料,在我们卷帙浩繁的《二十五史》中多不多呢?回答说,不多。这大概与欧洲当时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的许多史料是封建社会的产品——这一点有关。
足够说明问题的史料不足,调查统计数字不足,又往往不精确。对待这些“天然的”缺陷,人们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采取实用主义,把历史看做是可以随意乱摆的一堆大钱,钻史料有缺陷的空子,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任意发挥主观随意性。“四人帮”也是这样的做法。另一种是采取谨严负责的态度,从既有粗略资料中展转推求更可用、更精确的资料出来。随便举个例。谭其骧先生从许多资料中推求出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大批北人南渡的比例数字,是北方大约每八个人中有一人南迁;到南北朝对立开始时,南方每六个人中有一人是自北方迁来的。【1】不管这几个数字将来也许还会有更精确的推算,无论如何,这种做法是对人有启发的,即从无数据提炼到有数据、从粗数据提炼出精数据,以供后来人的使用。这是值得效法的。
以上,谈了些评价性的见解。底下,准备谈谈正规史料中社会经济部分所占的形势。自然不可能全面地谈,只可能抓几个重点。具体说来,我想谈谈“四志”、“两通”、“三会要”。
所谓“四志”,是指“正史”中最前面的四篇《食货志》;这就是《汉书·食货志》、《晋书·食货志》、《(北)魏书·食货志》和《隋书·食货志》。这样提问题,很像是有意地在贯彻“厚古薄今”的原则;但其实不是这样。之所以重点提出这前面四篇,第一是由于中国土地制度史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典型的几种田制恰好在上古和中古上半段,宋以后就是尽人皆知的封建地主经济了;第二是上举四篇确实较以后各朝代所写的《食货志》更具特色些,特别是第一篇(《汉书·食货志》)。的确,《汉书·食货志》所具备的特点多些、突出些。第一,在断代史中设置专门叙述经济的篇章,这带有独创的意义;第二,将“食”与“货”分成两部分,前者是农业生产,后者是商业、手工业、货币交换,这样划分也是符合历史情况的;第三,《汉书·食货志》的作者看出了一条线,在叙述中反复申说,什么“三代”如何,“至秦则不然”,“汉兴,循而未改”。这条线是什么线呢?就是土地私有权巩固以前和以后的一条界线。在这条界线以前,私租和国税是合二而一的;在这条界线以后,私租和国税就分而为二了。《汉书》能点出这条界线,很了不起。
另外三篇,虽较《汉书》稍逊,但也仍各有各的特色。《晋书·食货志》是唐朝编写的,较当世晚出时间较长,但也有优越性,距离远可以看得更清楚,当朝的禁忌较少,源流式的叙述较多,如有关曹魏屯田,就既可补《三国志》的缺陷,又可与《三国志》中传、纪材料互相补充,使后人获得较完整的印象。《隋书·食货志》也有这方面的好处,如在均田方面,把北齐北周到隋的一段源流,表达出来了;在均田以外的其他经济方面,甚至将南朝也夹叙进来,使读者有“会通”之益。《(北)魏书·食货志》虽较前二者又有所逊色,但《均田令》还是著录了的。以上这四篇《食货志》,是我们搞“中国土地制度史”、特别是搞“三田”(井田、屯田、均田)特点的人,必须重点参阅和使用的。
所谓“两通”,是指“九通”中唐杜佑的《通典》和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所谓“九通”,是指唐、宋人私家篡辑的“前三通”和清朝专制主义大皇帝乾隆为了显示清帝国的强盛和他本人的如何“稽古右文”而不惜铺张浪费,聚集许多文臣以架床叠屋的做法搞出来的“续三通”和“清三通”(当时是“皇朝”三通)。有关这些,多属于史部目录学的范围,兹不多赘。为什么在这里突出《通典》和《通考》两部呢?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杜佑本人就是唐朝的理财大臣,对社会经济资料是熟悉的,他所创写的《通典》里,对经济资料很重视。马端临虽是一位蒙古统治下隐居的儒生,但他父亲在宋末接触过行政,在家内收辑了不少典籍,马端临著《通考》,在社会经济方面列了八个“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廛、土贡、国用),写了27卷,不但对资料进行了排比,并且还进行了加工,写入不少条作者的按语,这使《通考》不仅是一部资料书,而且包含着科研的成果了。故“九通”之中,当以“前三通”为犄重;“前三通”中,又当以《通考》为犄重,是我们钻研中国土地制度史者必读必查之书。至于郑樵的《通志》,价值也不低,其本人自负尤高,但其精华处偏重于中古族性源流的方面,在社会经济方面不太突出。
所谓“三会要”,是指宋初王溥篡辑的《唐会要》和《五代会要》,和清末学者徐松从明朝《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宋会要》。特别是后者,虽然它的内容极端复杂,原始档案状态很显著,丝毫没有经过加工和科研的迹象,但其中对宋代社会经济重要资料的蕴藏量是极大的。对于一些大部头的资料书,如对于《明实录》,使用的工作已经逐渐展开了;对《宋会要》,则迄未见对它的深入利用。总之,我们对中国社会经济资料,必须心中有数,哪些资料书是一般的,哪些是重点;哪些书的好处在哪里,它们的缺陷又在哪里。自然这种“心中有数”也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在不断地进行科学实验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摸深摸透,才能左右逢源,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获致到有用的成果。
注释:
【1】见《燕京学报》第15期(1934):《晋永嘉丧乱之民族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