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170周年回眸:百年苦难 百年抗争(三)
鸦片战争与江南社会:清季诗歌的双重“意象”
朱季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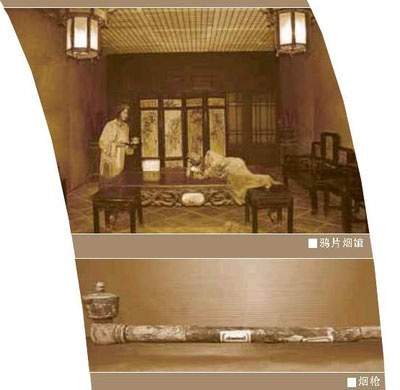


鸦片战争后,清季士大夫们通过诗歌,艺术性地描述了鸦片战争与江南社会的那段孽缘。后人可从中审析作者的心态与历史的环境,增进对这场战争的了解。
战争环境下江南百姓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是诗歌首先关注的内容。如1842年的南京,讹言传夷人将至,江宁将军德珠布即令闭城并构筑工事。过早的交通管制增加了百姓的恐慌情绪,先已自乱。“入城出城两不得,道旁颇有露宿儿。”(金和《守陴》)此时英军距南京尚有百里之遥。镇江城破,丹阳人心惶惶。“太守县令各传语,张官渡口险可拒,亟塞破船作防御。”(陆嵩《焚盐艘》)百姓已失去信心。对于汉奸行径,江南官府高度警惕。但矫枉过正,出现了很多滥指为奸、公报私仇的冤案。南京城内,“叩头妄指讐人家,一时冤狱延蔓瓜。”(金和《募兵》)民族之怨也裹杂其中。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对有嫌疑的汉民肆意戕害,一些汉族百姓为求自保,不惜登城呼救,盼英军破城。“枉民无故诛良善,揖盗翻教召寇兵。”(无名《京口驿题壁》)如此防民,令人心寒。
鸦片战争造成江南人口的减少与被动迁徙。如英军掠定海后,“舟山孤县东海东,兵燹之后人烟空。”(赵函《哀舟山》)镇江城破,侵略者进行屠城。“满城炮火摧墙堧,积尸盈路骸不全。”(杨棨《盂兰盆歌》)江南人对西方人的认知与交往远不如粤人,故对其描述也成为诗歌的主要部分。“白鬼黑鬼发毛卷,秽若负涂纵于豜。”(杨棨《盂兰盆歌》)厌恶之情跃然纸上。更多的江南百姓是通过侵略者的暴行了解这些“化外之人”的。占领城市的英军大肆抢劫与抓夫,勒索赎费。“鬼来捉去要钱赎。”(姚燮《捉夫谣》)并在各地抢劫富户典铺,“绅商铺典召寇兵。”(无名《闻警纪实》)
战争使江南沦陷区的社会经济遭受了重大的摧残。“可怜几辈经营力,付于江头一夜潮。”(严鈖《感事》)农业生产完全破产。“江南禾黍地,半为芦荻州。”(黄燮清《雨》)社会秩序荡然无存。“逃户炊烟空,劫掠尽鸡狗。”(贝青乔《过余姚县》)游兵溃勇的劫掠奸暴之罪行,随处可见。“溃卒仓皇工劫掠,残民潦倒避诛求。”(吴嵰《吴淞口》)英军入江南,有割断大清财源命脉之虞,“财赋三吴地,频年水逆流。”(孙衣言《出师四首》)财源之地顷成资敌之所。
清军战力的下降与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是诗歌揭露的重点。陆嵩在《夷船入乍浦烟贩闽奸杀青皮军以应》中描述汉奸的出卖造成乍浦的最终失守,“御敌但用青皮军,倒戈忽出乌烟谍。”朱琦更是痛斥“寇至军已逃,兵多饷空糜。”(朱琦《定海纪哀》)诗歌批判身居高位者怯战求和。“大府拥兵救不得,金缯日夜输鬼国。”(朱琦《吴淞老将歌》)英舰泊瓜洲,为防英军入城,扬城绅商与英军议和,送牛、羊等物及银一百万两馈敌。世人以其为怪谈,“究竟扬人无见识,苟延残喘亦奚为。”(无名《闻警纪实》)其实以金买安非扬州独创,镇江丹阳皆有所为。此现象也反映了在官员失职、行政权力出现真空时,江南士绅群体在地方社会结构中的强势地位。
江南女性多娇弱,但战争让女人无法走开,流传几多巾帼传奇。镇海之战,葛云飞战殁后,其妾率众抢回其尸。“不负将军能报国,居然女子也知兵。”(汪美生《葛将军妾歌》)身为弱者的中国女性在一场中国男人失败的战争中除了演绎几出激壮戏外,更多地则充当悲情角色。为保清白而捐生者众多,如乍浦刘凤姑遇辱时,“誓不屈,痛詈求死,遂遇害。”(褚维塏《烈女凤姑歌》)江南女性遭受炮火与礼教的双重压迫,除死,难有他途,这是清中期以来江南地区长期理学教化浸染的结果,也是战争环境所致。
诗歌也寄托了江南百姓对和平的渴望。“天兵指日应南下,速救生民水火中。”(无名《闻警纪实》)议和事成,对中国人造成的心灵冲击是巨大的。诗歌于此深感耻辱。“汉家表饵和戎策,越国缯纨沼敌谋。”(魏源《秋兴》)也对当事官员不满,“闻说卫青重作将,谁知魏绛又和戎。”(严鈖《扬州感旧篇》)1848年,英人有事往金陵,登岸游览,“路人瓦砾互投掷,鬼面流血争逃生。”(陆嵩《夷船复入江居民震恐》)也是民间情绪的一种宣泄。
战争结束,创伤很快被遗忘,江南社会重弹往昔靡靡之音。诗歌对此时发警惕之音。“流离莫问当年事,呜咽重添父老哀。”(黄燮清《闻督臣收定海》)进入清季的江南社会在此短暂的宁静后,再无宁日。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