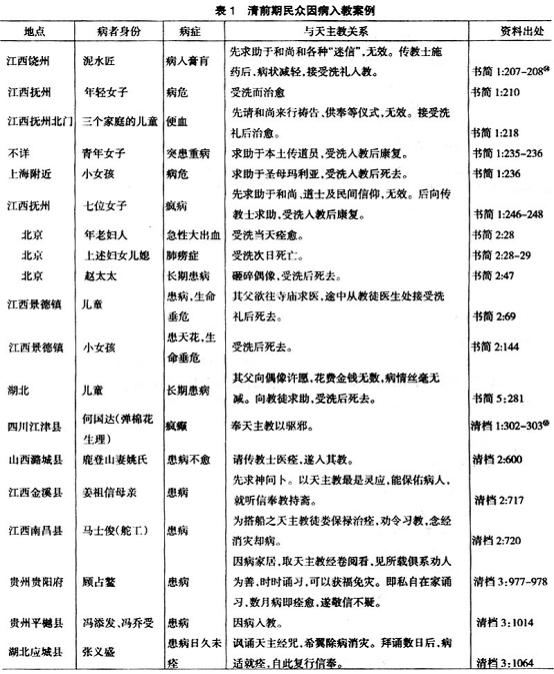清代前中期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社会环境
清代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比以往历史时期更为深入和广泛,云贵地区社会环境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背景主要有:一是随着行政、军事控制加强,王朝治边思想和政治举措在边疆地区逐渐深刻化;二是规模性移民及开发,使边疆地区总体上呈现出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局面;三是以矿业为主的生产与贸易活动,以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带动了边疆地区的深入开发,并形成有利于全国市场的自然资源商品化结构。
检讨以上历史过程的发生,从根本上看,都脱离不开制度变革这一重要背景,突出的表现是清代前中期对云贵地区的行政制度建立和改土归流等政治治理。尽管存在着局部地区不尽一致的变化状况,但在政治、经济过程等综合影响下,云贵地区获得了长足开发,充分显现出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调整对边疆地区治理的重要性。国内外在对清代云贵两省地方行政、疆域调整、改土归流等政治过程的研究,最具代表的是方国瑜、龚荫等人的成果,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严谨和翔实的史料爬疏,整理出比较系统的上述政治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变化。①而在有关这些政治活动、制度职能和行政意图及背景分析上,大林太良、真水康树、施坚雅等亦有过重要讨论,②特别是真水康树,对清代前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变化原因作了深刻论述,堪称经典。但是以上先行研究出发点和所依据的史料几乎都是中央王朝自上而下的审视,对地方实态,特别是制度在地域社会现实构建问题缺乏细致研究③。近年来整体史观和地域社会史研究勃兴,目的之一就是复原区域历史进程的整体面貌,视角更为全面和向下,本文基于此展开论述。
一、地方行政调整
清初针对云贵地区政治复杂局面,中央采取招抚土司,分化农民义军政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于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④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抵云南府城,“招抚流民,安插蛮庶”,“遂设院、司、道等衙门”,初步建立起中央控制的行政体系。⑤康雍两朝云南前明卫、所逐渐改并为府、州、县等行政建制,尽管在山区多设汛,分置塘、哨、关、卡,但在全省主要经济区的国家行政管理色彩愈来愈明显,表明中央对云南高原的统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雍正时期云南布政司领府二十三、直隶同知一、州三十一、土府、州各一,主要统治重心区域的行政设置基本沿袭前明,但在边缘区域,土司、土官的建制数目比明代明显减少。云南内地地区的中庆、曲靖、大理、楚雄、乌蒙、临安等,“自元迄近代之建置,无多改易”,而边地区丽江、北胜、永昌、顺宁、景东、元江、车里、临安广南等部分政区变动较多,反映了“政权逐渐巩固之过程”。⑥康熙六年1667年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间,云南地区有16个府级行政单位发生建置变动,调整面达到雍正朝全省府级数的66.7%。⑦就疆域而言,变动较大的是在雍正四年、五年1726、1727年,原隶四川的东川、乌蒙和镇雄三府经改土归流后分别划入云南六年〈1728年〉镇雄降府为州,隶乌蒙府;九年〈1731年〉乌蒙改名昭通,基本奠定了现代滇东北行政区划格局。⑧到嘉庆年间云南共领府十四、直隶州四、直隶厅四。
清初贵州因袭前明,领有十府。嘉庆朝以前贵州政区和疆域主要变动,一是将卫、所改归、设为府、州、县,加强和扩大布政司管理体系,这主要发生于康熙年间,绝大多数卫所被归并于布政司体系。⑨范承勳《改设州县疏》有言:
兹据详报称:查黔省卫所,康熙十一年间已将清平等五卫改县,安庄卫改州。现今尚存十五卫十所,其间有专城者,有府、州同城者,有与州、县犬牙相错者,军丁耕田纳量与民无异。所当分晰,裁并改设,如偏侨卫在镇远一府两县之间,查施秉县民粮稀少,将偏侨卫裁并施秉县,仍属镇远府管辖;……兴隆卫地错黄平,应将兴隆卫裁并黄平州,移州于卫治管理,驿站仍属平越府管辖;……新添卫附近贵定县田赋无多,应将新添卫裁并贵定县,移县于卫治管理,……。⑩
二是省界的调整,由于前明贵州设省主要出于控驭西南的军事目的,“滇无黔则扼其吭,蜀无黔则掣其肘”,11几百年来疆界与湖广、四川、广西和云南邻省犬牙相错,内部还存在着大量的插花地现象。12清初西南政治局面逐步稳定,疆界错乱的局面已不利于国家行政管理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黔处万山中,土不厚于西北,财不富于东南,而其地则在所必开”,13需要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来充实贵州地方实力。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割湖广镇远、偏桥二卫归黔,雍正五年1727年改湖广玉屏、清溪、天柱、开泰、锦屏五县归贵州;雍正七年141729年又将四川遵义府改隶贵州,15在政治和经济上增强贵州实力,“新收四川割归遵义一府五州县”户口30 884户,此数几占贵州雍正十年1732年新增户口69 518户的近一半。16康雍两朝对贵州省界的调整,基本奠定了现代贵州疆域范围。到嘉庆年间,贵州“共领府十二、直隶州一、直隶厅三”。17除上述调整外,康雍时代实行改土归流的云贵局部地区,也在地方行政和疆域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在高原腹地的毕节地区,康熙四年1665年吴三桂平定水西,改设流官,置平远、大定、黔西三府,与同期设流的威宁府合称“水西四府”。18滇东北、滇西北和滇东南原土司地区也改流设府。值得注意的是,后来乾嘉年间云贵地区设置了一批直隶州、直隶厅,云南有广西、武定、镇沅、元江四直隶州和永北、景东、蒙化、腾越四直隶厅;贵州有平越一直隶州和仁怀、普安、松桃三直隶厅。这些直隶州厅在云南的设立,基本上全在滇西北、滇西南和滇东南等先前实行过改土归流或相对偏远地区,除腾越由州升为直隶厅外,其余均是降原府为直隶州厅,19据《清史稿·地理志》至清末云南直隶厅州大抵也是在以上地区设立。清雍正年间曾对我国行政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主要是将明代复式三、四级政区层次简化为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三级制。云南的特殊性就在于直隶州厅的设立多由降府而来,而一般直隶州厅应是从散州或属县升级而成的。20
清前期在云贵地区实施的地方行政调整,非常强调通过行政和军事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在地方实行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创造条件,这可从康熙年间田雯、高其倬等地方大吏就黎平府与五开卫关系调整的建议中看出:
国朝康熙中,巡抚田雯以府隶黔,卫隶楚,同城非便,且黎平为苗多民少之地,设有机宜,两地盼悬,呼吸未应,疏请统归一省。后总督高其倬亦疏言:贵州形势,都匀以东,黎平以西,中夹生苗一区,名曰古州八万,地大苗众,正须料理,以五开归黔,则一切措办呼应即灵;若拔黎平归楚,凡有调度,必失事机。21
非常微妙的是,在此之前的贵州、湖广交界区域,府卫各属两省,每每割湖广卫所归黔,则黎平等布政司政区则归楚;当黎平等府归黔,则卫所复归楚。到清代这种现象随着对古州等“苗疆”之地的征讨,以及政府对苗区的控制能力加强后发生改变,府卫统归一省的呼声日高,最终卫所改设归为布政司体系成为主要。
注:1表中分境裁并,实为卫所分境屯赋裁并;2分境并入江川县、武定直隶州时间不详,表中依大多数的裁并年份,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3、4据康熙《楚雄府志》卷1《地理志·沿革》;5表中康熙十一年1672年贵州卫所的裁改,吏部议复是在康熙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据《清圣祖实录》卷37,康熙十年辛亥十二月初一日条。资料出处:乾隆《贵州志稿》卷1《黔省开辟考》、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1-29、光绪《滇南志略》卷1-6。
清代前中期云贵两省地方行政和疆域的新变化,给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通过改土归流等对地方行政制度作出的重大调整,对民族地区原生态产生深远影响。虽然制度变迁的作用和效果,有着一个逐渐深刻化和具体化过程,而且地域社会的改变非一时之事,但在清前中期云贵地区的行政和疆域变动,端显比以往更为深入、细致的政治谋略。
二、改土归流
因稳定边疆的需要,顺治、康熙两朝并未对云贵地区土司制度进行大规模变革,对土司的政策较为灵活,还未上升到动用武力征改的地步,少数的设流活动也仅出于土司绝嗣和平定叛乱缘由。顺治帝在对待云贵土司问题上称:“朕将以文德绥怀,不欲勤兵黩武。”22朝廷官员也认为对土司应“暂令各从旧俗,俟地方大定,然后晓以大义,徐令恪遵王制。”23即便在平定吴三桂后,康熙也未答应地方官吏要求征剿土司的请求,认为控制“苗蛮”等少数民族“惟在绥以恩德,不宜生事骚扰”。24这些思想较为符合中央王朝初涉云贵地区管理复杂民族、社会的实际需要,对于暂时稳定边疆和地方社会有重要意义。此外,维持土司管辖现状也保护了地方民族上层集团的利益,元明以来中央王朝和地方民族上层集团利害关系往往是一致的,彼此存在着依赖性,所以土司制度在清初得以存在和发展。25但是,随着国家力量和移民开发的不断深入,土司制度下超经济剥削,繁重的劳、兵、杂役和严厉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土司、土目反复无常地与中央对抗,到康雍时期已开始危及边疆政局稳定和地方经济发展。
所谓土司,“世其土即世其民”,在其领地内拥有绝对权力,其下土民处境悲惨。26乌蒙地区土府“其钱粮不过三百两,而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27东川等地受土司势力影响“川民不敢赴远力耕,滇民亦不敢就近播垦。故自改土以来,历今三十余载风俗仍旧,贡赋不增”,28“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29姚安府土司勾结流官,巧立名目,科派钱银,强抢民田,云南丽江木氏和贵州水西安氏有千百户被土司强占耕地而沦做家奴的农民,均破坏了刚刚起步的地主经济。30贵州“官取于苗者十之三,土司通事、差役取于苗者十之七,取苗民之精血以供其宴安酖毒之资”,且在黔东南一带尤为严重。31雍正初年云南额征钱粮不敷支应,多靠外省调剂,钱粮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司不识调剂,夷人不知稼穑”等“人事”所致,土司制度已对地主经济在云贵民族地区的发展形成阻碍,并影响到国家和地方赋税收入。32更为严重的是,土民反抗土司的斗争、土司之间的仇杀和土司反叛等行为直接影响了中央对地区的控制,激化社会矛盾和危害地方稳定。雍正四年1726年,深得雍正帝赏识的鄂尔泰出任云贵总督,与前几任不同的是,鄂尔泰一开始便“著《实政四条》:一戒因循;一严朋比;一重彝情;一正风俗”,33作风强硬,并对土司提出了一整套治理方案,认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雍正帝批准了建议,并先将时常反乱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由四川划归云南,由鄂尔泰节制。34不久,又令鄂尔泰署滇、黔、桂三省总督,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与前明和顺治、康熙朝不同的是,雍正时认为历代“相沿以夷制夷”法已经不合时宜,改土之法更加强调直接付诸武力,“欲改土归流,非大用兵不可”,35以求彻底铲除土司势力,因此雍正朝改土归流的范围和力度均史无前例,对地域社会的冲击也尤为强烈。
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集中在四年至九年间1726-1731年,涉及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和湖广等省,重点在云贵,而滇东北、滇南和黔西、黔东南、黔南等土司首当其冲。雍正四年,鄂尔泰进军滇东北东川等地,“云南路近,声教易及,凡滇黔两省商民有力能开垦者,广为招徕,以实其地;并将附近营汛斟酌移驻,以资弹压”,36连败土军,“乌蒙稍抗,即拟进剿”,十二月设乌蒙府、镇雄府,并设镇安营,驻军控制。到雍正八年1730年,平定滇东北地区,完成改土归流。37在雍正四年至九年大规模改流阶段,云贵地区共有10余个较大的土司被改流,不少是武力征讨来实现。38在黔东南等“苗疆”地区,雍正时期开辟“新疆”,认为“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徧加剿抚不可”,清军遂数次开进苗疆地区,对反抗的“苗民”实行血腥镇压。39尽管清廷在黔东南等地的军事行动,没有像在滇东北那样明确地指向某一实力强大的土司,但安屯和设流活动也成为雍正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雍正朝激烈的改流活动完成后,一些实力较弱的土司也纷纷归顺或被肢解、废除,使得18世纪中叶后中央对云贵地区直接行政管理的地域比以往有了极大扩展,这也是云贵两省在清中前期地方行政发生较多变化的重要和直接原因之一。
由于军事征剿和以武力威胁进行的改流活动占有相当的比例,特别是对实力较强的土司如滇东北禄氏付诸武力的军事行动更甚,因此改流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摧毁了少数民族上层集团对一部分地区的长期统治,如滇东北改流最终“杀掉了敢于顽抗的土官土目上百名”,40更多的土司举家被调离原地,“安插”于内地诸省,这为国家直接统治土司地区和筹划重建地方社会创造了条件。但是,对于当地少数民族下层而言,设流并将他们全部纳入国家行政体系因绝大多数“并未编丁”,这种管理存在着很大的形式意义41,使之客观上摆脱了土司制度的束缚,促进了地方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而言,取消土司制度后,中央和地方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善后措施,初步对千百年未受大规模冲击的地域社会进行了改造。
三、地域社会重建问题
学界一般认为,清政府通过编丁、保甲等措施,“将实行了改土归流的地区与中国内地一视同仁,通过调查人口,实行保甲制度来重新构筑地域社会”,乃至改土归流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汉化”手段。42但是,改土归流不仅是政治层面上的制度变迁,也具有社会、经济、文化等变迁的文化移入涵义;特别是对于地域生态而言,土司制度废除后,地域生态能否构建起实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转变组织和机制,甚至它们又如何实现“内地化”?都应是改土归流历史过程研究的重要组成,然而以往对此的研究着力不多。
清廷改流运动实为“除患”,消除对民族地区进行直接、有效统治的障碍。故在消除土司势力后,在原土司地区要“皆置营汛,形联势控”,在继续防范土司残余势力起事外,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43雍正、乾隆时期贵州“苗疆”是政府着力改归的重点区域之一,因受到地方强有力的抵抗,战事多,时间长,营、汛等军事布防格外重要,44在八寨、丹江、清江、古州等地安兵近万名,45目乾隆元年削平叛逆之后按:指雍正十三年包利、红银为首的苗民反抗,各处设屯安堡,分营制汛,防范周密”,46这在清代改土归流活动中是比较突出的。
广布汛塘关哨等军事防务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在加强对改流地区的控制时,因屯田和招垦等活动在山区形成移民潮,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的开发产生影响,这多为史学界所认识;二是多少弥补了民族地方因保甲推行难的不足见下文。但是军事布防在清中叶以后随着绿营兵制的衰败,汛塘体系名存实亡,在缺乏地方保甲支持或支持不力的情形下,改流地区社会控制和管理便出现“空壳化”,为流入之“奸民”同地方上层勾结成乱制造了条件。
出于盘清民情和削弱土司势力等政治目的,改流后政府开展了清理人口、田地等活动,如云南丽江府在雍正二年1724年设流后清出二千三百四十四丁,均来自土司庄奴。47其他各地亦有查办人丁的情况,但尚有许多仍未编丁入籍,这在保甲推行资料中有反映。在改流地区推行的保甲,“保甲之法旧以十户为一率,云贵土苗杂处,户多畸零,保甲之不行多主此识不知”,鄂尔泰建议“除生苗外,无论民彝,凡自三户起皆可编为一甲;其不及三户者,令迁附近地方,毋许独住。则逐村清理,逐户稽查……”。48在“苗疆”地区所推行“各寨编立烟户册,每十人为一甲,择以老成者为甲长,给以委牌;每十甲为一保,择以强干者为保长。”49需要注意的是,所见保甲之法大多是官员奏议,是否有效贯彻需要仔细考证。由于“生苗”等“难驯”,以及少数民族为避战乱而躲进深山,保甲实际上并未在地域社会得以广泛实施。仔细判读史料可以见得,实行了保甲的地方多是客民聚居区、汉民和部分少数民族错杂聚居区而已。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有称,“令夷人与民错处者,一体编入保甲”。50《清史稿》所载内容更为详细,亦言:
及乾隆二十二年,更定十五条:……一,苗人寄籍内地,久经编入民甲者,照民人一例编查。其余各处苗、瑶,千百户及头人、峒长等稽查约束。一,云南有夷、民错处者,一体编入保甲。其依山傍水自成村落者,令管事头目造册稽查。一川省客民,同土著一例编查。一甘肃番子土民,责成土地查察。系地方官管辖者,令所管头目编查,地方官给牌册报。其四川改土归流各番寨,令乡约甲长等稽查,均听抚夷掌堡管束。51
虽然保甲编丁和户口清查不是一个体系,但少数民族户口的缺编入册,也反映了保甲推行的实际困难,因为保甲编丁是以户口登记为基础的。52在改土归流地区,清代方志中保甲主要是针对汉民和部分“归化”了的“夷民”,不同于民国时期调查资料和方志中对少数民族保甲编丁记载较多的情况。实际上道光年间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此类情况,“昭通府俱系夷户,并未编丁,岂在当时仅联乡里而人丁数未报耶?”53这已不仅仅是户口缺编的问题。而地方官向朝廷奏请中,保甲之法主要还是针对客民,“黔省汉、苗杂处,近来客民渐多,非土司所能约束,自应编入保甲以便稽察;除生苗多之处仍照旧例停止外,其现居寨内客民,无论户口、田土多寡,俱著一律详细编查。”54
即便到清中后期,云贵地区土目、小领主等仍有较多存在,这些土司制度残余对地方仍有强大的影响力。赵翼《簷曝杂记》卷4《黔中倮俗》称:
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盖自祖宗千百年以来,官常为主,民常为仆,故其视土官,休戚相关,直如几乎天性而无可解免者。……。贵州之水西倮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孙为头目如故。凡有征徭,必使头目签派,辄顷刻集事。流官号令,不如头目之传呼也。
水西地区改土归流后并没有实现领主制向地主制的完全转变,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有制度仍大量存在于彝族社会。55水西地区改流后,“四十八目”影响力依然很大,流官管理体系的实施不尽顺畅,正所谓“土司改流官,土目仍世业”。56在土地和社会关系上,受地主经济影响,原土司地区孕育了“土目田”等特殊形态,土目是“土目田”的所有者,一般分给其子民“苗人”佃种,这一关系实际上更多的是维持或保留了原土司制度下“领主”经济生产关系,“苗人”身份仍带有明显的农奴或佃仆性质。
《黔南识略》有载:
关厢内外多豫章荆楚客民,乡则夷多汉少,今之自谓土目者皆安氏裔也。
自改流后均系报亩入册,与齐民等,无所谓土司,亦无所谓土目也。其支庶错居府属者,沿其夷俗。凡其祖报垦之田土,悉归长子承受,名曰土目;其或以私积别置田产者,亦概谓之土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重曰更苴,次则慕魁、勺魁、骂色,以至黑乍,各有司事,其服色与汉人无异。土目有婚丧等事,则敛派佃户,谓之派扯手。甚至同里及附近田地之粮户夷民,有被其强压者,不从则捏为叛佃,讦控不休。而争继夺产,好斗健讼之风彼此效尤。57
威宁州其民夷多汉少,汉人多江南、湖广、江西、福建、陕西、云南、四川等处流寓,各以其省设一头人;夷人则有土目,其次曰得暮、麻色。土目多安姓,大约田多而佃户众者,即称土目,非官设也。夷民俱听土目约束,地方有命盗案及征粮等事,皆责成土目协差分办如乡约。58
从上述地方实态来看,尽管改土归流活动使国家行政的直接管理模式在民族地区逐渐得以建立和巩固,但由于民族生态的复杂和保甲、赋税体系并未完全或有效地在民族地区普遍建立,一些民族地方社会实际上处于管理上的“真空”范围,给地方官吏勾结土司蚕剥土民和客民创造了机会,从现存的硃批谕旨中我们仍能看到许多清廷对地方吏治进行规劝和警训的相关记载。由此引发出的许多社会问题,在贵州地区还为后来咸同年间苗民起义埋下了伏笔,这应是清政府改流的局限之一。
那么,地域社会怎样才能真正实现重建或有效纳入中央行政、赋税体系?一方面是设流本身起到的行政建置的管理作用,如上文中论及的经制府州县设立;一方面便是学界传统认为的改土归流经济、社会等范畴实施的“善后”措施了。59事实上,作为改土归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恢复生产,增加税赋,是巩固和发展地方制度变革的重要保证。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生产的措施,主要以开展屯垦来保证政府赋税收入和巩固改流成果,使得改流地区在根本上确立了新的政治管理模式,这其中移民开发的贡献最大。
清政府在改流地区实行的垦荒活动,主要由驻军、招徕至的外地农民、土著居民构成,此外部分流民也有加入。雍正六年1728年清军进驻东川,“岁收二万余石,课矿岁万金,资兵饷。”60八年1730年,又“乌蒙地广田多,应将无业田地,每兵赏给三十亩,或有余丁,准其倍给。并量与牛种银两,劝令开垦”,开始在滇东北地区实行军屯。61九年1731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昭通“招募习于耕家之民及原住土民,每户给田或土二十亩,令其垦荒,自耕而食,开垦殖之端”,组织民户开垦。62昭通一带在雍正平定后“迁徙云南曲靖二府之民,至昭填籍”,63从各省调工匠修建城池,“城工既竣,遂相率留籍而为昭通人。”64到乾隆初年,昭通一带已“外省流民佃种夷田者甚众。”65清政府在贵州苗疆开辟后实行的垦殖活动,却有着与云南以上地区不同的特点,即主要采取军屯形式进行垦殖,并未像在滇东北那样积极鼓励和资助“夷民”垦殖。贵州古州安设屯军后,地方文武官员“设法劝种杂粮”,农隙时在山坡荒地“督令开挖,并令于堡内及山上空地多栽茶、桐、腊、桕等树”,还兴立市场,按期贸易。66在张广泗治理时期,苗疆屯军垦田总数在七万亩以上。67垦殖活动的大力开展,促进了地主经济对原土司地区领主经济的取代。清查、没收和变卖土司土地,进行新的土地分配,客观上在民族地区扶植了一批新兴地主,一些原本无地的夷民也获得部分土地,逐渐转变成为自耕农。据乾隆《云南通志》卷10《田赋》载,改流后镇沅、威远、东川、昭通、丽江等府就清理出土司领地681 232亩,这些土地或赐予地方官吏,或入官变卖,也有归还农民和分给农奴耕种。镇雄在雍正七年1729年时有六万多亩地变价入官,“先尽本佃户限半年之内照则缴价,如过半年尚或迟延未缴者,另觅买主缴价给照,令其永远管业”。68
在移民充实和政府督导下,经济开发还带动了汉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播,使原本土司制下“恐土民向学有知,不便于彼之苛政,不许读书”69的情形发生变化,各地普遍建立了学校,儒家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生活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比如儒学传入川滇黔边区后,新兴的彝族地主改汉姓,放弃传统的父子连名制,使家支制度走向衰落,原有的宗法制度发生了一些新变化,风俗变化也趋向于汉化。70清人刘慰三称鄂尔泰、高其倬等在昭通力办的三件大事之一便是:“易猓习,化旧俗之犷悍”,71移风易俗和传播汉文化使民族地区“内地化”,有利于清政府管理。
四、结论
清前中期在云贵地区大规模府卫、疆域调整和改土归流等政治地理变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先前时期,为18世纪中叶开始的云贵地区新一轮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奠定了基础。改土归流活动及其反映出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和实际,说明此期国家行政直接统治在民族地区逐渐得以建立和巩固,但由于民族生态的复杂和清政府保甲制、赋税体系并未完全或有效地在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对于基层民族社会而言,在部分地区仍出现因行政体系不畅或缺失而导致的社会管理问题,可视为改流的局限之一。虽然改土归流表面上是在对土司地区实行政治、社会制度的重新构建,但实际上仍由改流后的移民开发来弥补和最终完成,应视为改土归流等政治过程的深刻化,是清王朝有效治理云贵等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体现。
注释:
①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对于云贵两省,两位先生都有重要论述,但是在行政调整的年份、地区,改土归流的具体年份、土司裁撤,卫所裁并年份、地区等上,研究仍不够细,部分还缺乏具体所指。
②[日]大林太良:《中国边境の土司制度につぃての民族学的考察》,《民族学研究》1970年第35卷第2号。[日]真水康树:《明清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明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与清十八省行政系统的整顿》,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G.. W. Skinner,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 The City in th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77.在设立直隶州、直隶厅原因方面,施坚雅和真水先生都认为雍正朝时期变数最大,基本上都是基于军事控制原因而在地方设立直隶州、散州,只不过真水先生进一步指出直隶州、散州的设立还是财政税收方面的因素使然,并不等同于直隶厅仅侧重于军事考虑。真水先生还对改土归流等在云贵地区的实行进行了考证,但仅做数量变化上的分析,且不如龚荫先生细致。
③这个问题近年来尚不见其他学者予以讨论,笔者关注较早,可参见拙文:《制度变迁与地域社会:清代云贵地区改土归流和民族生态变迁新探》,《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④《清世祖实录》卷41,顺治五年十一月辛未。
⑤清倪蜕:《滇云历年传》卷10。
⑥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77、782、783页。
⑦由于篇幅问题,本处不详列变动情况,资料出处为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5《云南统部·建置沿革》、光绪《滇南志略》卷1-6。贵州地区,自康熙四年1665年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间有11个府级行政单位建置发生变动,占嘉庆朝全省府级数的68.8%,资料出处为《清圣祖实录》卷15,康熙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条;卷18,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条;卷20,康熙五年丙午十一月十一日条;卷113,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十一月十九日条;许缵曾:《滇行纪程·水西四府》;乾隆《贵州志稿》卷1《黔省开辟考》;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99《贵州统部·建置沿革》;《黔南识略》卷24、25、26。
⑧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5《云南统部·建置沿革》。
⑨乾隆《贵州志稿》卷1《黔省开辟考》。
⑩清范承勳《改设州县疏》,见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卷20《艺文一》。
11乾隆《贵州志稿》卷1《黔省开辟考》。
12对贵州插花地的调整主要集中在晚清时期,可参见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
13乾隆《贵州志稿》卷1《黔省开辟考》。
14遵义府改隶贵州,今从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99《贵州统部·建置沿革》。而乾隆《贵州志稿》卷1《黔省开辟考》、乾隆《贵州通志》卷11《食货志·户口》、《黔南识略》卷30均作“雍正五年”。
15乾隆《贵州志稿》卷1《黔省开辟考》。玉屏、清溪、天柱、开泰、锦屏五县归黔,乾隆《贵州志稿》作“雍正二年”,然《黔南识略》卷15、18、23各县均作雍正五年,所载改归翔实,今从之。
16乾隆《贵州通志》卷11《食货志·户口》。
17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5《云南统部·建置沿革》、卷499《贵州统部·建置沿革》。
18《清圣祖实录》卷15,康熙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卷18,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清许缵曾:《滇行纪程·水西四府》,《丛书集成新编》本。
19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75《云南统部·建置沿革》。
20周振鹤:《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页。这个现象值得关注,尽管周振鹤先生并未进一步指出原由,但是笔者认为云贵的直隶州由府降设背景是不同于真水康树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财政税收方面的原因,而主要出发点仍是军事控制。这种解释回归到了施坚雅的结论上来。说云南直隶州设立因军事而非财政税收,重要的证据可以追溯到明代和清初这些地区设立的较多的“巡检司”上。
21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1《黎平府》。
22《清世祖实录》卷75,顺治十年五月庚寅。
23清王弘祚《滇南十议疏》,见康熙《永昌府志》卷25《艺文一》。
24《清圣祖实录》卷124,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庚子。
25[日]大林太良:《中国边境の土司制度につぃての民族学的考察》,《民族学研究》1970年第35卷第2号。
26清田雯:《黔苗蛮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8帙。
27清魏源:《圣武记》卷7《土司苗瑶回民·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7册《云南巡抚鄂尔泰奏陈东川事宜折》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此言“自改土以来”,是指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东川土府曾实行改流,但“仍为土目盘踞,文武长寓省城”,流官并未进驻,徒有其名见魏源:《圣武记》卷7《土司苗瑶回民·雍正西南夷改土归流记上》。
29清魏源:《圣武记》卷7《土司苗瑶回民·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8册《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土司夺佔民田流官串合贿断折》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张捷夫:《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载《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
31民国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第1编《总论·军事初起时贵州之背景》,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聚珍仿宋版印。
32清倪蜕:《滇云历年传》卷12。
33清鄂容安:《襄勤伯鄂文瑞公年谱·雍正四年丙午》。
34《清史稿》卷288《鄂尔泰传》。
35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2《鄂文瑞佩三省总督印》。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7册《云南巡抚鄂尔泰奏陈东川事宜折》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37清魏源:《圣武记》卷7《土司苗瑶回民·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38武力征讨在雍正朝以规模大而相对较为突出。受篇幅所限,本文不详列各改流事件,但据道光《云南志钞》卷7、8,《清史稿》卷512、514、515和龚荫《中国土司制度》爬梳、统计,有清一代云南有38起土司降废事件含无嗣停职,其中“讨灭、讨平、诛灭”等有14起,占总数的36.8%;据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7-8、龚荫《中国土司制度》爬梳、统计,贵州发生降废土职事件有74起含无嗣停职,其中明确记载为“诛灭、讨灭”等的有4起,尽管此仅占总数的5.4%左右,但却包括了对大土司水西宣慰司等的武力征讨。事实上,发生武力征讨的事件仍是较多,上述统计所取是直接导致停职的状况,不少土职的降废是经过不断的反复征讨来实现的。
39《清史稿》卷512《土司一》。
40王缨:《鄂尔泰语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1正所谓“土民事事有土例”清人赵翼言,见赵翼:《簷曝杂记》卷4《土例》。改土归流对民族社会的冲击并非无所不在,国家统治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深刻化”也有局限,民族内部有其自身的一套长期实行的社会管理体系近现代民族调查显示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所说在改流后地域社会的构建,更多的应是指国家对地方统治秩序的建设和民族交往体系的改进,对于民族社群内部并不一定“重建”了新的社会文化模式。
42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
43清政府在云南一些较为发展的内地,将汛设城内,分塘哨于山区;边远地区因人口稀疏,山区荒芜,则多设汛分置塘、哨、关、卡。可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29页。
44《清世宗实录》卷52,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45《清世宗实录》卷89,雍正七年十二月戊申。
46《清高宗实录》卷249,乾隆十年九月二十九日,贵州提督丁士杰奏。
47清倪蜕:《滇云历年传》卷12。
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7册《管云贵总督鄂尔泰奏陈宜重流官职守宜严土司考成以靖边地管见折》雍正四年初六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49光绪《古州厅志》卷3《屯政》。
50光绪《滇南志略·总叙》。
51《清史稿》卷120《食货志一·户口》。
52学界一般认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起的云贵地区户口数才比较可靠,但少数民族,特别是土司地区人口尚难完全登记造册。李中清认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政府才正式登记少数民族,不过直到1776年前仍因“行政制度”上的原因而在不少地区缺乏登记。见[美]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载《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
53民国《昭通县志稿》卷2《食货志·户口》。
54《清宣宗实录》卷99,道光六年六月三十日。
55方国瑜、史继忠、余宏模和潘先林等对彝族社会改流后遗留的“则溪”制度和土地制度均有过深入研究,本文不详述。则溪制度,产生比土司制还要早,可以说是水西彝族社会制度的核心,它将彝族社会的宗法制、等级制、世袭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严密的政权、兵权和族权的统一。土司制仅为中央赋予的管理形式。土目田地制是则溪制受地主经济影响下在经济生产上的反映形式之一。而温春来、黄国信等的研究还表明:尽管历史上有汉人等跻身贵州西北彝族社会“勾”的政权,且经清初军事征剿和“保甲编户”等,但土目等形态所反映出的旧的“彝制”仍在地方民族社会发挥作用,甚至到近代以来依然在“历史记忆”和“现实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参见温春来、黄国信:《改土归流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以贵州西北部地区为例》,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76本第2分抽印本。
56清黄宅中:《谕土目》,见道光《大定府志》卷59《文征九》。
57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4《大定府》。
58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6《威宁州》。
59关于改土归流“善后”概念,笔者认为应纳入改土归流“过程”一说,可参见拙文:《制度变迁与地域社会:清代云贵地区改土归流和民族生态变迁新探》,《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60清魏源:《圣武记》卷7《土司苗瑶回民·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61《清世宗实录》卷96,雍正八年七月乙酉。
62民国《昭通县志稿》第十一《农政·垦殖》。
63民国《昭通县志》卷6《氏族志》。
64民国《昭通县志》卷10《人种志》。
65《张允随奏稿》,乾隆七年二月十七日。
66《清高宗实录》卷105,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67潘洪钢:《清代乾隆朝贵州苗区的屯政》,《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4期。
68清徐德裕:《条议镇雄事宜禀折》,见乾隆《镇雄州志》卷6《艺文》。
69清张广泗:《设立苗疆义学疏》,见乾隆《贵州通志》卷35《艺文志》。
70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71页。
71光绪《滇南志略》卷4《昭通府》。
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2008年4期第39~48页,中华文史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