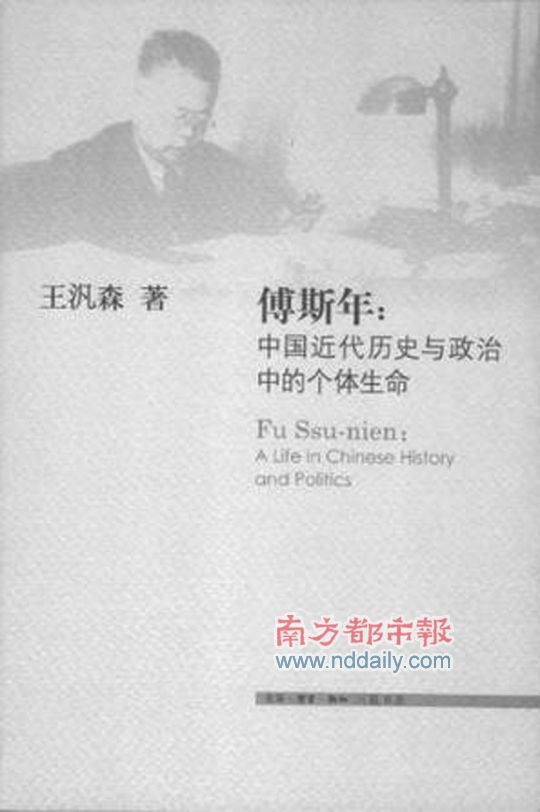王汎森:傅斯年是一个时代的表征
王汎森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汎森著,王晓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版,45 .00元。
王汎森与老师余英时先生
王汎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台北中研院副院长、中研院历史语言所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明代中期至1950年代思想史、学术史及史学史研究。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等。
很多人知道王汎森,可能因为他2005年在台湾花莲教育大学做的一个演讲———《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在演讲中,王汎森事无巨细、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差异、研究生期间又当如何。之后王汎森在讲稿基础上写了一篇文章,流传甚广。能产生这么大影响,王汎森始料未及,他曾开玩笑说,生平写过的文章中,没想到,最为人知的竟是这一篇。
这当然是自嘲之语。王汎森成名非常早,从台大历史系研究所毕业后,他径直进入史语所工作;后又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追随余英时。年轻时的王汎森极富才气,加上文笔又好,很早便获得学界关注,当时甚至有人称他为“小余英时”。
正是在余英时的影响下,王汎森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明清及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我的兴趣还是在了解:是什么历史因素造成了今天的我们?这就牵涉到近世中国。”王汎森在史语所个人名录的研究自述中写道:我的“近世”从明代中期一直到1950年代,关心的重点是思想、学术以及文化的历史。只要是这几个世纪中的问题,我都有浓厚的兴趣。
“传统与现代之争”是“近世中国”最为重要的命题,它如同一个巨大漩涡将整个中国社会都卷入其中,喷发出巨大的能量。王汎森被这个命题所吸引,先后写有《章太炎的思想》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以及他的博士论文———《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傅斯年》今年五月已经由三联书店在内地出版。在中译本序中,王汎森提到,“余(英时)先生提醒我,不必大幅转述傅斯年学术论文中的观点,如果想了解其学术观点的人,自然会去读他的原书,要紧的是把它(学术观点)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看。”
王汎森严格遵守了这些原则。“思想和生活间有密切的关系。”王汎森曾谈到,傅斯年生活在一个过渡和动荡的时期,那样的生活情境跟他思想变化,有很密切的联系,思想与政治、社会、教育、出版、风俗、日常生活之间,是一种佛家所谓的“互缘”。
虽然《傅斯年》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著作,但王汎森彼时的观点仍然延续至今。“龚自珍《释风篇》说:‘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之一,便是捕捉‘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的流风。”王汎森在自述中谈到。
角度:不以崇拜者的角度写傅斯年
南都:《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是你在二十几年前写就的,能否给我们谈一谈写这本书的过程、点滴?
王汎森:这本书的英文版写于二十几年前,我记忆中当时并没有完整的傅斯年专书(英文或其它语言都没有,中文的则有论文集)。因为我是史语所出身的,所以写傅斯年时内心有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在我初进史语所时,许多老前辈都还在,在他们心目中傅斯年是神圣不可讨论的人物,挖掘任何他的真实的生活史材料,都有一点亵渎,我到现在还记得编辑出版《傅斯年文物数据选辑》(1995)时内心的忐忑紧张。
所以我不是以崇拜者的角度写傅斯年,我的态度毋宁是比较接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中所说的,想了解“主体对事物的知识如何可能”,我的书是想了解傅斯年及他所代表的事物在近代中国“如何可能”的这一点上。
南都:现在回过头再看这本书,有没有觉得遗憾的地方?
王汎森: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设想的是西方学术界的读者,所以它免不了有许多限制。首先是语言。我认为当时在英文书中没能较细微讲述傅斯年在建立学术事业时的做事风格,没能细细状写傅斯年在谈及学术工作时常用的“措词”。譬如他常见的口头禅是“集众的”、“现代学术标准的”、“有组织的”,不是零散地推展学术“事业”。这些措词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新学术的擘画者、奠基者与领导者所标示的品位与标准,而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代学风。
定位:“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人物
南都:传记与个体研究之间的差异表现在哪里?你认为好的传记写法是怎样的?
王汎森:我曾经非常心仪包斯威尔《约翰生传》(内地译为《约翰逊传》)那样的传记,曾经想用这样的方式写一本梁启超传。因此我曾经以《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为基础,做了许多工作,今天看来恐怕没什么价值了。
这不是一本详记生活历史的传记,而是思想传记(intellectual biography)之类的,主要是看整个时代的脉络与个人思想、行动之间循环往复的交互关系。一方面看这个人物的思想与行动,如何重大地改变那个时代的论述,同时也要从这个人物看到那个时代,从那个时代看到这个人物。
论文交出之后,余英时老师似乎照例要有一篇评估报告交给系里,但我始终未曾看到。余先生说他在报告中提到,这篇论文的主角最像英国大史家纳米尔(L e wisN am ier)。比较遗憾的是因为书的性质限制,我并不能将傅斯年为人的个性及处事的风格,尤其是他如何成功地做一个史语所所长这些部分写出来。那些是比较像《约翰生传》中的东西。
南都:你将傅斯年定位为“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含有“历史”与“政治”两个维度,你是怎样考虑的?
王汎森:我是以傅斯年作为一个时代表征,讲一代人的历程,譬如:在书中,我曾特别提到傅斯年到欧洲留学,从某一个角度看,是去开启许多大门,但也是去把他人生的几扇门关起来。我知道这话很重,并不一定恰当。学术化、纪律化是一种进步,其贡献毫无疑问,但是另外有一些角落是被封闭起来的。这与当时欧洲的一股强大的实证主义思潮的力量有关。
赴欧洲留学之前,傅斯年天赋的强大感受力与想象力,得到最朴素、甚至有点天真的表达,从他在《新潮》时期的诗、文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而这种天真烂漫的想象力,在回国之后有些部分被关闭起来了。
我觉得这不只是傅斯年一个人的情形,在许多人身上也表现出来,它使得五四时期的激进心态有一种转向,也使得后五四的“新学术的建立”有一个清楚而有力的表达。
南都:“新学术的建立”在当时的作用何在?在它的理念下,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具有哪些特点?
王汎森:“新学术的建立”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对于传统色彩还非常浓厚的民初社会而言,这个阶层既有一点熟悉又相当陌生。熟悉的是新的学术阶层与传统的“士”很相近,也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陌生的是他们追求的学术,带有强烈的专业性、科学性,有些“无用之用”的学理,往往不一定是眼前或日常生活所熟悉、或所能立即应用的。他们的关心往往看来与眼前的关心有差距,这种种现象使得这个新崛起的阶层,在带有传统色彩的在社会看来有时是高度的钦仰,但许多时候还带着一些陌生、不解、羡妒交加,或严重疏离的感觉。这个新学术阶层的崛起是近代历史的一件大事,也因为它的崛起而形成了许多的两难。
我在书中展示了许多两难,有的并未明说,希望读者心知其意。这些两难使得他们这一代知识人有一种特有的张力。
譬如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在两种节奏间摆荡不定时,移植新学术、新思想时那种无所不在的两难。日用与精深研究的两难、学术结论与政治需要的两难、耗时费日的专业工作与致用与否之两难,尤其是学术研究与民族主义之两难。最后这一点事例尤多。傅斯年深受德国史学影响,“民族”是他拿手的大题目,他有一束未刊稿,即题为“民族与古代中国”,他基本上主张民族的多元组成,宣称“中国民族是混合的”,并认为应以此为傲。可是在抗战时期,这与政府的主调相背。
我其实是想刻画一种内在的两难与紧张,不想将这一个时代的这种紧张、两难掩盖下去。这不只表现在傅斯年一人,也表现在许多人身上。我们过去总是把时代考虑得太平滑、太纯净了,忽略了这种内在紧张与疑难,以及这个两难之下的意义。
此外,傅斯年的经历,从早年的五四自由解放到后来的statism (我的英文书中第六章的标题用此字,但中文很难确译),似乎与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后来的转向有可对比之处,也就是说他这一代人的经历,涵盖了日本两、三代人间的生命历程,因此从这一个案也可看出比较广泛的意涵。
辩证:“一团矛盾”带来的痛苦与益处
南都:作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傅斯年为何最终又选择了学术道路,并且立志在中国建立新的学术传统,建立一个全新的学术社会?
王汎森:学术的落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傅斯年从学生时代起便属于学问型的人物,而不只是口号型人士,所以他在《新潮》的发刊旨趣书一再强调,要知道西方的学术“美隆如彼”,而中国的学术“枯槁如此”,用一句现代人的话说:“学术的落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这句话其实不只是傅斯年的想法,它表达了戊戌以来许多人心中共同的想望。
今年三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第四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时,在餐宴上有一位学术先进突然说,如果不是五四那一辈人物,我们今天的自由、民主、学术都是不可能想象的。他所说的是常识,可不知为什么有一种特别真切的感受。我们对五四及近代的新学术传统可以有许多批评、补充,但它的重大意义是不容轻忽的。
傅斯年最初对史语所的设想是半实体化的。当时把研究员的地位设想得很高,大概等于院士,必须是各学科中的全国代表人物。最初的构想是以中研院研究所作为帮助全国同行进展所学的基地,他在给高本汉等人的信中皆一再强调此点。而且傅是非常清楚地要以现代西方的学术建构作为范本来建所,譬如他常谈要仿照高尔顿实验室(G altonLaboratory)来建立体质人类学。
此外,他非常重视任何一件研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意义”。1938年讲到天文所从北平迁到南京的古仪器中有明成化年间仿郭守敬之两件仪器,他说:“乃世界科学史上之宝器,亦是中国科学史上之第一瑰宝也。”还有他常用的措词如“借西方学问之路径”,提倡几种学问(如提到G alton,如英国的院士制),或强调“有组织的学问”,与没有组织的学问之间的差别等。而且重视比较的观点,希望人们能多得异国历史比较之益,譬如他主张把伊拉克的“驻札大臣”与汉王国的“相”相比较即是一例。
南都:你对傅斯年概括为“一团矛盾”,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一团矛盾”?
王汎森:如果我记忆无误,我在与林毓生先生的谈话中他常强调“痛苦”(agony)是学术或思想创发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每一个时代许多人内心中不免都有矛盾。但傅斯年他们这一代还有前后几代人,其内心世界基本上宛如两列对开的火车,冲突、矛盾的情形严重。
有许多人被矛盾折磨、压垮,但我总认为有许多事物是“啄啐同时”,有其利的同时也带着某些弊,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也有某些人在折磨之余得到一些好的、附带性的结果。对后者来说,我觉得有几点:一、“一团矛盾”的状态也可以转成一种“内在的张力”,而创造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内在张力。二、我一直服膺王国维的名言,中学西学进则俱进,这一代人的许多“矛盾”,其实是来自他的旧学与西学素养的紧张,而这种学问上的张力及互相支持的关系下,往往有很大的创发,傅斯年的许多论文正展现了这个特色。三、困思的样态之一是内在各种资源之间的矛盾,但又善用这些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之间也可能产生对话而激发一些原先所无的火花,借用乔布斯(SteveJobs)形容他一位朋友的话,他可以在自己脑海中开会。此外,矛盾的各个面,大部分时候是互相抵消的,但换一种心态、换一个角度,也可能变成是多元资源组织成的一个有机体,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
在这里我仅举一例,譬如傅斯年常叹他早年太受“国文”之累,说“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但后来又说从事整理国故工作时,“但不曾中国文先生毒的人,对于国故整理是有些隔膜的见解,不深入地考察,在教育尽变新式以后,整理国故的凭借更少。”这就是一种矛盾的心态,而这种矛盾在他看来是有益的。
“一团矛盾”而无出路当然非常折磨人。钱穆《师友杂忆》一开始写到许多早逝的朋友、同学,我常以为这些人恐怕就是不堪于“一团矛盾”而被压垮的人。
考据:傅斯年“如何做一个所长”
南都:傅斯年被很多人称之为“学霸”,你怎么评价?
王汎森: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有一位教授R ogers H ollingsw orth研究科学家的创造历程,他提到最好的学术领导人是既开明但又有权威,而且时常可以用他的权威破格给予有创造力的属下特殊的支持。我觉得傅斯年领导史语所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因为他具备了上述的特质。
这个题目使我想起已故剑桥/普林斯顿大学的汉学大家杜希德教授(D.Twitchett)的一篇名文《如何成为一个皇帝》(How to BeanEmperor:T‘angT’ai-tsung‘s Visionof His Role)。我记得当年杜氏后人将他的藏书送给史语所时,李远哲院长在致词中便说他也知道杜希德先生的这篇文章。这使我觉得应该谈谈傅斯年“如何做一个所长”。
《如何成为一个皇帝》主要是指唐太宗对他自己帝王角色的看法,但针对傅斯年,应该写一篇《如何做一个所长》,而这不只是要从宣言性的文字去分析,还要从日常生活史料,包括笔记、谈话去了解。我发现傅斯年在书信中最常提到的是“事业”、“标准”两词,即他非常清楚他正在努力的是为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学术“事业”,这样的事业在过去是不这么做的。另外他处处要提出一个“标准”:包括用人的标准、学术的标准,在这些标准的导引下希望发展出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拟的学问,而且在一开始把“标准”垫高了,以后的学术事业便容易建立了。
傅斯年的书信中有很多谈到用人、晋升等的标准,或甚至是做事的标准,这些零星的材料有重要的意涵———譬如傅斯年是那样尊敬陈寅恪,可是抗战期间,当陈寅恪不能按照公家的规定回所而是在桂林教书时,傅斯年坚决不肯支付全薪,而且不准中研院总办事处打马虎眼,甚至到了大吵的地步。
傅斯年与人通信中,另一常见的问题是人才:培养人才、把人才送出国去读书见世面。以当时中国财政之困难,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最费钱也最缓不济急,但傅斯年近乎强聒不舍地要政府各个机关挤钱出来做这件事。衡诸这些人后来的成就,也证明了培才、养才是一件要不计代价去做的事。
我曾经在台大的一场演讲中把傅斯年对治所的策略综合成六点:一、不拘一格识拔人才。二、尽量将人才放在手边。三、如守黄金般守住人才(如芮逸夫、丁山之例)。四、以侍候一群有学问的人在身边尽情工作做为职责。不过傅斯年的标准很严,他严格区分专心治学者及不专心治学者,譬如抗战时傅斯年认为闻一多、王献唐非常专心工作,总寻思着要给予一些补助。五、催成绩、出书,用最高的标准出书,印书水平要超过欧美、日本,用他的话说:“倾家荡产印集(书)刊。”六、要懂得宣传。为了宣传史语所的成绩,华人方面是仰仗胡适,洋人方面抓紧伯希和(Paul Pelliot,著名法国汉学家),就是好的例子。此外,学术远见、突出而严格的学术标准、找钱、找人、留人、资源之寻获,也都是傅斯年每天的工作。
他在处理所务时,集细部想象与规划之最,包括如何做木箱、如何省运费、如何省旅费,真可谓“丁宁周至”。傅斯年最长于写信,用信来指挥事情,这让我想起张居正。我偶尔重读《张居正集》,对他用书信指挥、动员各地官员的印象相当深刻。傅斯年因长期不在所内,史语所的工作又常常散在多处,故不知写多少信指挥、调动,信中虑事周密、精到,真使人吃惊。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要岑仲勉离所南返那封信,虽因重大扞格而不得不分手,但读来仍情味无穷。信上说:“先生不忮不求,学问之外一无所涉心,足以夙兴,弟尤钦慕。今以一科上之不同,遂各行其所是,亦事之无可奈何,望先生不以此事为怀。以后敬乞时赐教言,不弃在远,固终身之厚幸也。引领西望,先生自此远矣。恻怛如何。”
南都:你也曾做过史语所所长,你最注意的是傅斯年做的什么事?
王汎森:在所有傅斯年所做过的事中,我最注意他催学术成绩这一件工作。傅斯年往往是没命地催,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催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傅斯年有一封信上说这部书拖了十五年,再这样下去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还看不到书出版。又如他催于道泉的成绩,简直到了要反目成仇的地步,后来于道泉终于交了一本《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Lovesongsofthe sixthDalailam a),应付过去了。我对藏学不懂,但是十多年前有人告诉我这还是于道泉最好的著作。
我在担任所长的六年间,见了人就要催成绩,催到最后有些人怕与我见面,有些人明白表示苦不堪言。严肃的学术成绩出产最慢,动辄要花一二十年,譬如最近李宗焜的《甲骨文字编》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几年,在我任内,每年我都要问几次,而每次过年前他都回答说定稿快送出去了,最近这四巨册的书终于出来了。另一位同仁用法文写近代法国人类学历史,在法国得了大奖,这本书也似乎与我“见面就催”有关。这类例子非常多,我总以为对研究学术的人而言,“时间永远是不够用的”,有人在身旁催促还是一件好事。
评价:“学霸”傅斯年,到处成为一种力量
南都:但你仍没回答“学霸”这个问题。
王汎森:首先我必须说,如果在引用前面所提到的威斯康辛大学那位教授的研究,即“权威”非常重要,那么“学霸”一词也可以有很好的意思。
我们知道汉学的发达与若干“宗主”或“宗座”型的人有关。譬如纪昀、翁方纲、阮元、毕沅、程恩泽等都是,官位不一定要非常高,譬如程恩泽即只是侍郎而已,但是人们认为他与道光时代的多才多能之士的养成关系非常重大,至于阮元之为乾嘉汉学之“宗主”人物,更是不待说了。
我曾大致归纳了一下阮元为什么能做一代之“宗主”。首先是自己要拿得出几种压得住人的著作,标举一个特定的学术宗旨或标准,不断地集合有才学之士做有重要学术意义的“集众式”的重大工作,如编《经籍纂诂》、《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并校勘记》不断地识拔有才学而位处卑微的年青学者,为他们到处揄扬或找出路。要不停地获取资源,不停地识拔年青新进人才。要不停地出钱或出力,帮忙某些贫寒的学者刊行他们或前人的有价值的著作。这一点在清代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学术出版机制并不健全。有时候甚至要用自己的权威强力去办某些有学术意义的“闲事”。我记得阮元为了从焦循后人身上将书板逼出,好将该书印出以飨学界,写了一封信给对方,其口气已近恫吓。但是为了学问公家之事并不避讳。民国固然与清代不同,不过在上述方面,傅斯年也都有具体的例子,使得他成为当时学术界强而有力的宗主型人物,或者称为“学霸”。
这里要套用傅斯年给人信中的一句话:“天下事是傻子干出来的!”我认为这句话跟胡适说:“(傅斯年)到处成为一种力量”讲的是同一件事,也可以用来说他之所以成为“学霸”的理由。好的“学霸”的要件之一是得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去帮忙他人成就他们的学术事业。
所谓帮忙他们成就自己的学术工作,在这里我要举傅斯年在谈到史语所同仁的成绩时的口气为例。在李庄时,傅斯年有一封信大意说见到一些同事的新成绩,说可以大解国难之窘忧,如见到董作宾在《殷历谱》之进展,一方面暗喜,一方面还要设问题以难之,故意挑一下,让大家都得到一种学问的刺激与兴味。又如看到陈寅恪的论著中发现李唐祖先非汉族血统,觉得是一个大创获,为之狂喜,认为足以解消抗战之烦闷等。不时以催促、欣赏、鼓励的态度去帮助他人成就一种共同的“事业”,也是做一个“学霸”所不可少的。
不瞒你说,我个人在整理傅斯年书信出版时,发现傅斯年几乎无日不在与人争论。一位曾经与傅先生共事的人说,抗战胜利后,为了傅斯年坚持要办“伪学生”、“伪教授”,把他们这些教育界的主管弄得灰头土脸。傅斯年从来不怕为了原则与人争执。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到整顿北大一定要去除北大教授中的某种势力,而他愿意身任其事“与之周旋”,由此可以看出一点梗概。不过史语所的老前辈高去寻先生告诉我,陶希圣曾说过:“傅斯年活着时,人们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
当下:史语所学风有承有变
南都:史语所是如何走出傅斯年的影响的?又如何来保持当年自己的特色?
王汎森:今天史语所与傅斯年的时代不同。一个机构经过了七八十年,其学风必然要有承有变,不承则不成为一个学派,不变则不能维持它的时代性。以法国的年鉴学派为例,它几乎与史语所同时创立。在1990年彼得·伯克(Peter Burke)写《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时,便借用了一位年鉴学派史家的话,说这个学派经历了“从地窖到阁楼”的三次大变化。史语所亦有许多变化,在史语所七十五周年时,我写了一篇《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中便把我当时所观察到的变化作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后来我策划了一套《中国史新论》(计划出十册,可惜至今尚不能出齐),这套书中所规划的主题,有许多是史语所创所时不特别关怀的,譬如性别史、基层社会、思想史、医疗史、科技与社会、生活与文化等。
以思想史为例,我刚进史语所时做过一两次明代思想的报告。当时只有黄彰健、黄进兴两位是同行,黄彰健先生告诉我,早年他研究理学思想时,在所里真是一只孤鸟。虽然傅斯年1940年出版《性命古训辩证》时,其实已经在治思想史了,但所中这方面的趋向并不明显。黄先生说他1950年在杨梅时,傅斯年先生看了他一篇讲理学的稿子,点点头表示可以,他才放下心来。然而在1980年代以后,史语所里面思想史的空气蛮盛,这就是与以前不同的地方。这种研究领域的开拓与变化现在还一直在进行着。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这里面还有“承”,即延续性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管做什么题目皆本“实学”之精神,要用“排山倒海的证据”来支持论证。
最后,让我最感诧异的是过去十多年,我遇到过几位西方及日本的读者,不约而同地说读完这本英文书时受到“感动”,我认为这应该是客气话,而且他们是在说傅斯年不是在说我。我猜测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傅斯年的个性、生命、悲壮的历程使他们觉得“感动”;第二种可能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许多人对于史学家追求历史事实已经不感到兴趣,或不再有信心,他们却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中看到传统史学信念强韧的力量。
来源:百道网2012年0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