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家庭]生计安排——《中国家庭史》第四卷第三章第二节
第三章 家庭生计
第三节 生计安排
这里的生计安排主要是指家庭的生产性安排,大体包括普通家庭对生产时间和资源的调配,家庭劳动力之间的分工协作。同样因为时间和篇幅等因素,我们的讨论主要以当时占家庭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家为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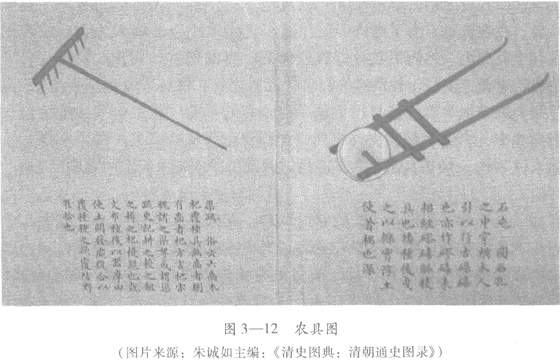
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属于温带和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而农业是一个季节性很强的产业,故而,当时农家的生产安排首先是围绕着季节的变化而展开的。关于一年四季农事和家庭生产的安排,当时有不少的文献记载,这里选取了其中的三份来加以说明。
(1)《沈氏农书》关于明末浙西地区的家庭Ft常事务安排的记载。《沈氏农书》作者为浙江湖州涟川镇的沈氏,具体为谁不详,撰于明末崇祯年问,后由浙江桐乡的张履祥补辑刊刻。书中所述反映了浙西和江苏太湖地区的农事状况。该书首列“逐月事宜”,按月叙述家庭农事等生计安排。其内容概述如下:
正月,主要工作为三项,一是垦田、翻土、准备肥料等为日后土地种植作准备,二是种桑秧、修整桑枝、给麦子和油菜浇水施肥等养护过冬作物,三是置备农具、蓑衣箬帽以及糟烧酒等饮食。
二月,继续上个月的农事准备等工作,另外,开始整治秧田,并嫁接桑苗,劈柴换炭,在地里下瓜种,在池塘巾下菱角种,买小鸭,雇好忙月的人工。农事开始逐步展开。
三月,除继续农事准备和照顾过冬作物外,主要农事活动进一步展开。开始播种梅豆和晚豆,种瓜秧和芋艿,垦花草(即紫云英,可用于施肥和做猪饲料)田,浸泡谷种,整治秧田,雇工修理水车,腌芥菜。茶叶上市,置备茶叶。

四月,进入夏季,农事全面展开。做秧田、下谷种,收割油菜麦子,买粪进一步给桑地施肥,播种和管理各种蔬菜,腌青菜,买蚕蚁入池喂鱼。
五月,农事正忙。继续管理各种蔬菜,给大田施肥,拔秧种田,同时收拾油菜子,整理桑枝,出售大麦,买苎麻布、蒜(醋用),腌梅子,熏杨梅。
六月,农事正忙。收割梅豆(用手拔),翻垦菜地,管理稻田,预订冬季做羊饲料的枯桑叶,准备菜肴,比如晒酱、做瓜干、做豆豉等。
七月,入秋,农事稍闲。主要工作为管理稻田和桑地,同时下麦秧,并种菜。
八月,农事较闲。主要管理菜地和种菜,同时准备收割稻子的工具,农闲时,做泥砖(即砌砖坯,家庭副业)。
九月,进入收获季节,忙月。主要收割稻子,整治稻场,拔晚豆,播种蚕豆,为种麦作准备,整治竹林地,孵鸡鹅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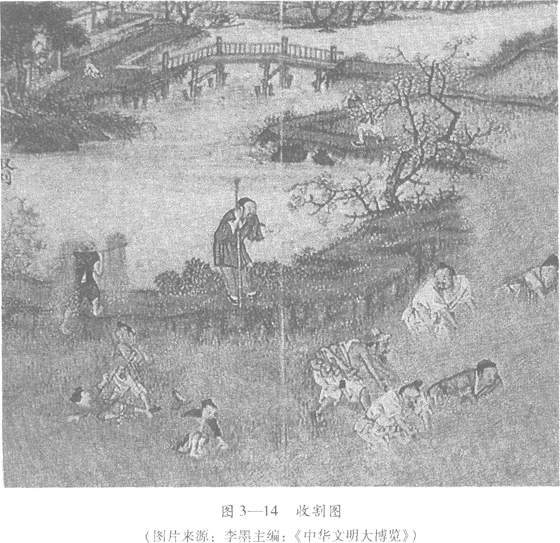
十月,入冬,继续收获,仍忙。仍收割稻子、用稻桶惯稻(即使稻谷脱粒)以及做米(即碾成糙米),播种麦子油菜,收获赤豆、晚豆,种芥菜、青菜,做菜干,酿酒。
十一月,农事渐闲。管理麦田油菜地,将糙米碾成精米,卖糠,准备副食,如做风鱼、火腿。
十二月,除管理麦田、菜地以及桑地外,主要整治副食,比如做酒、做醋等。[1]
(2)《家政须知》中关于清初山东地区的农事安排的论述。作者丁耀亢,字西生,号野鹤,以号行。山东诸城人,清顺治中曾以贡生官至惠安知县。与清初山东大儒王士祯有交往。《家政须知》是作者关于家庭生活的一些论述,附录于其诗集《丁野鹤诗钞》之后,由其子慎行校刻康熙年问。书中有“因时”一节,主要讨论一年农事的安排,认为这是“立身治家”的根本[2]。这一部分字数不多,谨抄录于下:
正月,布置农务。算一岁官粮之数。入学,课月程。修理房屋,更换阱牛,觅农工,勤夜作。
二月,乘冻移树,春风前后,栽种十日,接果树。课农春耕,修屋,动土功,播种锄麦田,省耕开仓。
三月,播种,相土地之宜,农功大作。停土功,滋养鸡鹅羊豕。浴蚕,修种菜圃,尽出积粪,修粪池。次开仓省耕,出粟贵粜,备官粮。修园囿,挑野菜,煮酒。
四月,课锄,养蚕,修水道,伐树枝,修仓窖以防阴雨,采树头作菜。三开仓省锄,载菊,种蓝,兮蜂。
五月,采药,收丝织绢,割麦种豆,墁墙壁。大修粪窖,以备积草。牧豕,栽竹,修桑树,制药,踏酒曲。
六月,晒麦,晒书画。课农取草作粪。修田间沟洫。动木工做家器,用漆。晒皮毡衣,作酱曲,插各样花,伐栎去皮下水,条桑。
七月,末伏出粪积粪,伏中早耕麦地,沤杂木,伐枯竹。再风书画、毡衣,收瓜子、苎麻。运种麦粪。
八月,天社前种麦,收芝麻,收稻。做毡货,裱书画。采葛,收松果、橡栗,剥枣。早秋耕,栽牡丹、芍药。
九月,割牛草,伐薪柴,烧炭御寒。收藁秸诸草卜垛,收干草备畜牧。收春初放出杂粮,及各庄籽粒入仓。锄牛脚草,酿酒腌菜。
十月,塞北户,修园仓,收远庄子粒入仓。计算各庄收放账目。积牛脚草,收山草上垛,为来春修盖。培果树,收野菜御冬。
十一月,酿来春酒,动夜功纺绩。牧猪上練。备祭祀,夜诵读。收芋,修牛屋,封仓。治农兵防夜。培竹。
十二月,修祭器、家庙。运割草入场,新炭出山。备交际礼物腌腊,贸易年货劳农。[3]
(3)《清稗类钞》中有关晚清苏南情况的描述。这份记录主要依据宝山县农人所述,并参以武进顾铁僧之言而撰成,内容如下:

正月,棉花地翻泥。或以人督牛,或人自为之。
二月,麦田菜地施肥料,种紫荷花草。
三月,捞水中草泥,捞时置之舟中。加泥于田塍,种菱养鱼。
四月,获麦,稻田布种,俗曰种秧田。种棉花,种芋。
五月,插稻秧,芸稻,人立于田中获跪,以手拔去其草,手或有套。稻田车水,棉花地削草,豆地削草,种黄豆,种芝麻。
六月,荡稻,荡,器名,一长方之木板也。其意义则移行也,动也。人持一器,立于田中,以器荡之,使泥悉平,有直荡横荡之别。稻田施肥料,豆饼菜饼及人畜粪也。如酷暑需加石膏。稻田戽水,棉花地削草,获瓜。
七月,搁稻,此与陶朱公书所谓田立秋后不添水,晒十余日,谓之搁稻者不同。搁稻之法,有荡扒之别,扒,器名,其形略如梳,以梳之。稻田戽水。
八月,获稻,获棉花,获绿豆,获豇豆,获芝麻,种竹,稻田有戽水者。
九月,获稻,获稷,种麦,种蚕豆,稻田有戽水者。
十月,获稻,种麦,种菜。
十一月,捕鱼,樵薪,垦桑地。
十二月,樵蒹葭,樵绿柴,为染料之用。种苔菜。[4]
另外,小说《醒世姻缘传》也有一段专门描述农家四季农事的文字:
立了春,出了九,便一日暖如一日,草芽树叶渐渐发青,从无乍寒乍热的变幻。大家小户,男子收拾耕田,妇人浴蚕做茧。……
挨次种完了棉花蜀秫、黍稷谷粱,种了秧,已是四月半后天气;又忙劫劫打草苫、拧绳索,收拾割麦。妇人也收拾簇蚕。割完了麦,水地里要急忙种稻,旱地里又要急忙种豆。那春时急忙种下的秋苗,又要锄治,割菜子、打蒜苔。此边的这三个夏月,下人固忙的没有一刻的工夫,就是以上大人虽是身子不动,也是要起早睡晚,操心照管。
才交过七月来,签蜀秫,割黍稷,拾棉花,割谷钐谷,秋耕地,种麦子,割黄黑豆,打一切粮食,垛秸干,摔稻子,接续了昼夜,也还忙个不了,所以这个三秋最是农家忙苦的时月。只是太平丰盛的时候,人虽是手胼足胝,他心里快活,外面便不觉辛苦。
说便是十月初一日谢了土神,辞了场圃,是个庄家完备的节候。但这样满收的风景,也依不得这个常期,还得半个月工夫。到了十月半以后,这便是农家受用为仙的时节,大囤家收运的粮食,大瓮家做下的酒,大栏养的猪,大群的羊,成几十几百养的鹅鸭,又不用自己喂他,清早放将出去,都到湖中去了;到晚些,着一个人走到湖边一声唤,那些鹅鸭都是养熟的,听惯的声音,拖拖的都跟了回家。数点一番,一个也不少。那惯养鹅鸭的所在,看得有那个该生子的,关在家里一会,待他生过了子,方又赶了出去。家家都有腊肉、腌鸡、咸鱼、腌鸭蛋、螃蟹、虾米;那栗子、核桃、枣儿、柿饼、桃干、软枣之类,这都是各人山峪里生的。茄子、南瓜、葫芦、冬瓜、豆角、椿牙、蕨菜、黄花,大园子晒了干,放着过冬。拣那不成才料的树木,伐来烧成木炭,大堆的放在个空屋里面。[5]
小说中描写的是明代英宗复辟以后山东一个叫明水镇的地方的情形,从上面的描写看,当时当地农家的生活过得辛苦而富足、自在。这样太平丰盛的生活恐怕不见得有很强的普遍性,不过以上资料至少可以表明,明清时期农家的生活是有张有弛,忙闲交错,_般来说,夏秋忙而秋冬闲,由于当时很多地区采用的是一年二熟制,所以特别是收种的两头,四五月和九十月尤其忙碌,土地较多的地主家庭一般需请忙工,而普通家庭也需要亲戚朋友之间相互帮助。而相对农闲的时节,农户也不会完全闲着,除了为农忙作一些准备工作以外,还会积极投身于家庭手工业,以上资料对此虽有所涉及,但较少正面论述。比如《沈氏农书》中只有种桑的描述,但对农家的养蚕治丝却只字未提。实际上,至少从明代中后期以后,民间的家庭手工业在很多的地区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清代文人王有光记录了一首青浦、嘉定一带的谚语,日“纺车头上出黄金”,并解释说道:“纺车,古时用以缫丝辟鲈,后世更有棉花成纱,皆由车出。其器甚微,而其利甚薄,一家内助,以济食力,此犹未足称出黄金也。此而绩之,为布为缯等物,足以衣被天下,妇习蚕织,不害女红,不扰公事,不致舍业以嬉,浸为风俗,不啻黄金遍地。”[6]而关于家庭治丝,乾隆《吴江县志》论述道:
绫紬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问,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丝之丰歉,绫绸之低昂,即小民之有岁无岁之分也。[7]
而吴地的一首民谣则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四月里来暖洋洋,大小农户养蚕忙。嫂嫂家里来伏叶,小姑田里去采桑;公公街上买小菜,婆婆下厨烧饭香;乖乖小孙你莫要与妈妈嚷,养蚕发财替你做新衣裳。[8]
又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江苏常州的例子,“冬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俗谓种田饭米。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之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9]可见,纺织等家庭手工业生产要占用普通农家相当多的生产时间。这样的生计安排无疑会使普通家庭的成员整体上相当忙碌,当然,我想也不能就此将他们的生活理解为终岁勤动,毫无闲暇,而且各个地区的情形也不一致。比如,从最近邵鸿、黄志繁发现的一本徽州婺源地区的小农家庭生产活动日记簿来看,农家“嬉”的时间并不少。这一日记簿为婺源县龙山乡一位上过私塾的农家少年林光钥记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根据研究者对日记簿的统计,林光钥本人全年休闲的日期为20天,占全年355天的5.63%,他父亲的休闲时间则达到117.5天,占全年日期的近三分之·(33.1%),而在家正式劳动时间只有113天(打杂除外)。林光钥本人之所以嬉的日子较少,可能与他的主要的劳动内容——牧牛有关。就林父的情况看,他二到七月相对忙碌,尤其是六七两月,几无空闲,其他月份较闲,其中又以八九两月最闲。这与我们前面资料反映的忙闲分配情况有所不同。工作内容方面,以粮食生产占用的时间最多,达62天,占总劳动天数的55%,其他依次为经济作物(茶)16天,蔬菜11天,另外还有24天做讨柴、作风水地等杂活。另有亲戚的帮工81天,特别是有个名叫“齐兄”的共帮工28大,不过林父帮别人劳动的时间只有2天。所以这种帮工应该不会是完全无偿的[10]。林父一年享有如此多的休闲,大概与其家庭不错的经济条件有关。普通农民的休闲应当不会如此之多。日记簿中未见从事家庭手工业的记载,由于其中完全没有女性活动的记载,所以有可能存在家庭手工业而末予记录,也有可能当地纺织等手工业并不盛行。于此亦可见到,全国各地的情况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同时,从上面的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当时农家的生计安排是相当精打细算的,对各种资源的利用也尽可能地充分。比如,《沈氏农书》中安排三月雇工整治水车等生产工具的理由为“前此同短,后此工忙”[11]。而且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生产的东西来制作各种菜肴,以避免花钱。并且还充分利用各种自有或公共资源来饲养猪、鸡、鸭等家禽和家畜,以备食用或出售。不仅普通农家如此,就是那些地主官绅之家也同样如此。由此可见,当时的家庭经济,尽管早已离不开市场,但在取向上仍具有比较强烈的自给自足色彩。
另外,当时家庭对家庭劳动力的利用方面,也是比较充分的。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虽然总体上并没有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但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作用已相当重要。对此,张履祥曾总结道:
(女工)随其乡土,各有资息,以佐其夫。女工勤者,其家必兴,女工游惰,其家必落;正与男事相类。夫妇女所业,不过麻枲茧丝之属,勤惰所系,似于家道甚微;然勤则百务俱兴,惰则百务俱废,故日:“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资其辅佐,势实相等也。[12]
不仅如此,作为家庭成员的老人和小孩也会被要求承担一定的劳动。小孩可能在六七岁甚至更小的时候,就被父母要求做一些辅佐性的劳动,比如拾柴、打草等。特别是女孩,由于一般都不读书,很小就开始练习女红、纺织等。比如明代庞尚鹏在家训中要求:
女子六岁以上,岁给吉贝十斤,麻一斤;八岁以上,岁给吉贝二十斤,麻二斤;十岁以上,岁给吉贝三十斤,麻五斤;听其贮为嫁衣。妇初归,每岁吉贝三十斤,麻五斤,俱令亲自纺绩,不许雇人。[13]
庞氏的要求基本是从培训其家庭女子的技能出发的,但在一些普通家庭,女孩的纺织实际已成为家庭收入的来源之一,比如,吴江自明中期后,“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故儿女白十岁以外皆蚤暮拮据以糊其口”[14]。清代在苏州、松江等地,“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15]。
由此可见,农家的生计安排整体上是非常经济而讲求效益的,正因如此,如果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汁算他们的收支状况,很可能会难以理解其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中很多人的生活固然不富裕,从账面上,很可能没有剩余甚至入不抵支,但正是这种经济与效率,使他们仍可能相对“自如”地生活下去。
注释:
[1]《沈氏农书·逐月事宜》,见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ll一24页。
[2]丁野鹤:《家政须知·因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l995年版,集部第二百三十五册,第402页。
[3]丁野鹤:《家政须知·因时》,“四库全书存日丛书”,集部第二百三十五册,第402页。
[4]徐珂辑:《清稗类钞·农商类》,第五册,第2254~2255页。
[5]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二十四回,《善气世回芳淑景好人天报太平时》,第355~359页。
[6]王有光:《吴下谚联》,中华书局l982年版,第77页。
[7]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丛书·华中”,第163号,第四册,第1132页。
[8]顾颉刚等辑:《吴歌·吴歌小史》,江苏古籍出版社l999年版,第501页,转引自张佩围:《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l48页。
[9]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力作之利》,“丛书·华中”,第426号,第52页。
[10]邵鸿、黄志繁:《19世纪40年代徽州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介绍一份小农家庭生产活动日记簿》,载《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7期,2002年4月。
[11]《沈氏农书·逐月事宜》,见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第15页。
[12]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补农书校释》卷下《总论》,第l51页。
[13]庞尚鹏:《庞氏家训》,见徐梓编注:《家训——父祖的叮咛》,第142—143页。
[14]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丛书·华中”,第163号,第四册,第1132页。
[15]尹会一:《敬陈农桑四议疏》,见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