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主户:有田产的农家——《中国家庭史》第三卷第二章第二节
第二章 “户”与家庭经济阶层
第二节 主户:有田产的农家
观察宋元时期乡村农家经济阶层的分布情况,看看富裕人家、维持温饱的中等人家、连温饱都难维持的贫穷人家各占多大比例,一个比较现成而又相对准确的角度,是从户等制度入手。户等制度是户籍制度的分支,为了按各家的财产多少有差别地征派不同的税役,把各个家庭划分为不同的户等的时候,需要详细登记各家的财产状况,并且在本乡或本县的范围内进行评定,这就客观地记录了当时各地乡村农家的经济实况和经济阶层的分布情况。我们从户等制度人手考察的另一个理由,是户等划分与经济阶层的划分还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或家族为单位划分的。
所谓经济阶层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概念,而且是一个不太确指的概念。从划分的依据上讲,与阶级的划分相似,都是依据家庭经济状况,但又比阶级的划分琐碎;从琐碎的程度上讲,与等级的划分相似,都划分为若干个层次,但又不像等级划分那样主要依据政治地位。所以,只能说经济阶层是按照各家的经济状况划分的,是按照各家的实际经济状况划分为若干个级别的方式。实际上,经济阶层的划分早就有了,古书上讲的富豪、贫民,人们习惯说的大户、小家之类就含有这种划分的意思,只是从宋代开始经济阶层的划分比以前明确了,甚至宋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总的来看,可以说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乡村农家经济阶层定型和明朗化的时期。
经济阶层明朗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主客户划分方式的第一次出现。在这以前,唐代有过主户、客户的说法。主户又称土户,指当地的土著民户,因为编籍纳税又称正户、税户和课户;客户指外来的人家、客寓民户,唐代有记载说“人逃役者,乡浮寄于(他乡)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1]其中有因为贫穷破产逃亡的人家,也有其他原因避居异乡的富户。在很长的时间内,主户客户只是区别当地人和外来人的一对概念。从唐代中叶开始,主户开始指有土地财产的家庭,不论田产多少,只要有田产纳税,就算是主户;客户则是一无所有、不承担官府赋税的贫穷人家,主客户的概念已经不再表示当地人和外来人,而是以有没有自己家的田产为标志了。这些主户是有田产的民户,有的是自耕小农,有的则是富豪家庭,但只要没有官爵,没有政治特权,其身份就与一般客户一样,“主户之与客户皆齐民”。[2]换句话说,主客户的划分在宋代已经是以有没有田产为标准,不再考虑是当地人还是外来户了,而且仍然与政治身份无关,主客户划分的仍然不是政治等级;主户在宋代也不全是地主,多数是自耕小农,所以又不能算是两大阶级的划分,仅仅是乡村农民家庭的经济阶层划分。
作为有资产的阶层,无论资产多少都包括在内,主户的范围相当大:除了两头,即少数权贵之家和一无所有的客户,所有中间家庭都属于这个阶层。主户阶层在宋代是承担赋税徭役的主力,为了根据各个家庭的不同经济实力来有差别地征派不同的徭役,官府进一步完善了前代的户等划分制度,通过民户的户等高下来决定税役的种类和数目。正是由于划分户等的目的是为征派不同的税役,不负担赋税的客户也就不再划入户等之内了,由此形成了与唐代以前户等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唐以前是划分所有的乡村农民家庭为三等或九等,宋代则剔除了客户,专门划分主户家庭为五等了;在传统的划分户等的标准——资产的多少——的基础上,第一次加上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基础性的标准——资产的有无。
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即有直系血缘关系、有共同财产的群体,在官方户籍上称作“户”。宋代户籍在登记各家的户口状况的时候,根据不同的需要有三种户籍分别登统:一是以征派田亩税即“二税”为目的的“二税版籍”,主要登记各家的田亩的数量、四至和方位;二是以征派力役和丁役为目的的“丁口账簿”,主要登记各家的丁口数目,特别是男丁;三是以征派职役差役为目的的“五等丁产簿”,登记内容包括田产和丁口,并且按各家的田产和丁口状况划分为五个级别(五等户)。在这三种户籍中,五等丁产簿与户等划分的关系最为密切,是专门的划分户等的文书。
税役是历代乡村农民家庭的最大的负担,常常因此而破产;即使到不了这种地步,把自己家的粮食和钱物交出去,或者去给官府无偿地干活,也是吃亏的事。所以各家都想尽办法减少承担税役,在宋代首先要设法降低自己家的户等,隐瞒家中的丁口和田产,所以经常存在户等划分“不实”的问题。登录五等丁产簿的时候以县为单位,根据征派税役的需要规划出二三年内全县各等民户的比例,然后由各乡村具体划分,各乡的户长、里正具体负责,划出以后上报给州县衙门。在划分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漏洞,所以到了北宋中期增加了一道手续,由各家先自己申报各自的丁产状况,户长、里正负责核实。各家自报丁产状况的账目称为“手实”,“按户令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田野居民,耆长岂能尽知其贫富之详?既不能自供手实,则无隐匿之责,安肯自陈?”为了让各家自己承担责任,还规定不如实申报要受罚。据说手实的登录很繁琐,所以只推行一年就废止了,[3]还是由户长、里正直接登录和编排。为了防止户长们作弊,“造五等簿籍,将乡书手、耆户长隔在三处,不得相见。各给所由子,逐户开坐家业,却一处比照”,然后取其中。[4]即使这样,各家还是设法降低户等,特别是有势力的家庭与户长们勾结,尽量隐瞒丁产,结果把税役负担转嫁到了中下层家庭,往往由此导致中下层民户家破人亡。宋代史书中的这类记载很多,有的甚至让“孀母改嫁,亲族分居”,以避免被划为上等户[5];还有记载说:“京东民有父子二人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6]衙前役由一等户充任,可能是这个家庭中减去一丁就可以降低一等,不用承担这个徭役了。本来一等户应该是相当于地主的富裕家庭,但是从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来看,却是个普通的中等家庭,这显然是上户转嫁税役负担、隐瞒丁产过程中的受害者。
不过,宋代划分户等的主要依据还不是人丁,而是各家田产的多少。登记各家田产的时候有的按田地和浮财分别登记,有时候把两者合并总汁作价,称为“纽记”、“家业钱”。
家业钱是把一个家庭中所有的田地、房屋、用具和浮财一并折算计价,入账的时候记为某家共有家业钱若干“缗”,然后再在家庭与家庭之间比较家业钱的多少,定出户等的高下。有关划分户等和按户等高下征派税役的记载,经常反映这种登统方式,元丰年间有的地方“上户家业钱多而税钱少,下户家业钱少而税钱多”,[7]有人上疏说这属于划分户等中的不合理行为。开封以及河北地区让民户代养官马,“坊郭户家产及二千缗,乡村及五千缗养一匹”,[8]乡村民户的家产在这里就是指的家业钱。还有的地方为了完成征派税役的任务而虚升户等,如定州的第四等户“民家之产仅能值二十四缗”,[9]比通常的标准少得多……都提到了家业钱的问题。北宋中期以后直到南宋对家业钱的登记越重视,哲宗元j;占年间提到家业钱的奏章比以前明显增多了,王觌说当时的情况是“既用家业钱而定差役钱之多少,则所谓等第者无所用之,而等第之民又不可废,故郡县之吏皆于家业账内率意妄说曰:自家业若干贯以上为第一等户,若干贯以下为第二等户,至五等十等皆然也”;吕陶建议保甲教阅必须“于三等以上或等第虽低,而家业抵一百贯方得差充”;风翔府“竹木械应募土人以家产抵当,及八千贯以上者宜押”。[10]直到南宋仍然使用这种登统方式。这可以说是宋代划分户等时登统家产的最常用的方法。可以想见,那些户长、里正之类的乡间小吏挨门挨户掂量估摸的时候,各家都会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财物,不能隐藏的就设法压低价值,与乡间小吏做生意似的相互争执;加之乡村家庭的传统习惯是不愿意显示富有,有了财物也尽量隐藏不张扬,现在被外人反复掂量,心里一定很反感而又无奈,这些乡间小吏因此也就成了各家各户共同防范和讨厌的人物。
分别登记田产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田地。登统田地也是以家庭为单位,有两种具体的办法。一个是直接登记各家的田亩数量,按数量多少来大致划分户等,有人反映说,“假如民田有多至百顷者,少至三顷者皆为第一等,百顷与三顷已三十倍矣”,[11]很不平均,就是讲的这种方法。在具体登统的时候,各乡在“本保打量田亩四至,勘会甚年月日产,主身死有无承分之人,即今何人为主,与下状同赴县”申报,[12]对田亩的多少、来历和将来的户主都弄得很清楚。南宋的时候还为此专门搞了一种七地清册,称作鱼鳞册,一家一册(张),连田亩的地形都画上去了。有时候为了更准确平均,还沿用先秦时期的划分“地等”的方式,[13]把田亩的质量也考虑进去。会稽一带人多地少,登统的时候极为细致,先划分田地的肥瘠等级,再按不同的等级折合成钱,然后登记总额,“第一等田亩记物力钱二贯七百文,第二等二贯五百文,第三等二贯文,第四等一贯五百文,第五等一贯一百文,第六等九百文。田亩有好怯,故物力有高下”[14],质量和数量都考虑到了。第二种方法是不直接登记田亩的数量,而是按田亩的税钱来计算,因为宋代的二税专门指田亩税,按二税税钱来登记比统记田亩更方便,所谓“田顷可用者视田顷,税数可用者视税数”,就是讲的这两种方法,哪个方便用哪个。为了方便,后来渐渐地都按税钱数划分了。浙东地区各州县“常以税钱,余处均以物力推排,不必齐以一法。用余额通以田地、物力、税钱、苗米之类,各令安排”,[15]官府不便统一规定,各家更无法自主选择,只能由地方州县规定具体的登统办法,多数州县都是以税钱为依据多少来划分等第,而且很不平衡,有的从一贯到十贯以上、或者从五贯N–十贯以上都划人同一个等级之中了。还有的边远地区按籽种数登记,或把田亩、田税折为布匹,按布匹数来登记,但这种方法在内地不见使用。
最苛刻的是登统各家的浮财的场合。各家的财物用品本来不便让别人知道,有些东西甚至是秘不示人的,但是由于划分户等,又不能不让乡长、里正这些人物登门入室,一件一件摆弄,把自家的“家私”全部展现给外人看,这本来够他们恼火的了;更有甚者,乡长、里正们对各类物品尽量往高价上估,对可记可不记的甚至根本不属于登记范围的东西也记在账面上。每三年(闰年)一次登统,对各家各户来说无异于被“抄”了一次家。

本来官府对“浮财”的范围有过规定,即除了田亩之外的房屋、树木、畜产和农具,都属于比较大的用物,但是这些乡间头目在实际操作中却不这么大方,“凡田间小民粗有米粟,耕薅之器,纤微细琐,务在无遗,指为等第”;[16]有的时候甚至连“鸡犬、箕帚、匕筋已来,一钱之物”都记入浮财之数。[17]“乃至寒瘁小家农器、舂磨、铚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输十,估万输百,食土之毛奠得免焉。”[18]有的时候为了凑足上等户的户数,“官吏籍其杯器、匕筋,皆计资产定数,以应需求。势同漏厄,不尽不止”;“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深山穷谷之民,一器用之资,一豚彘之畜,则必籍其值以为物力。至于农田亡耕具、水车皆所不免”。[19]这些相同的记载反复出现,说明在实际登统过程中浮财的范围是没有边际的,凡是家中有的,被乡间小吏们看得见的都可以计算在内。那些被登统的家庭不只是气愤恼怒,更有一种担忧和惧怕,他们不敢多置买田地,更不敢多置办家用物品,吕公绰在郑州发现,由于“籍民产第赋役轻重,至不敢多畜牛,田畴多芜秽”,[20]司马光在乡间看到“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粟,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锦,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21]再加上乡问小吏与有财力的富裕人家串通,“视其赂之多寡以为物力之低昂”,[22]最后让中下层家庭吃亏。所以这种登统家中浮财的做法是最让当时各家各户畏惧和厌恶的。尤其是因此不敢养牛了,使农民的劳动负担更重了,王祯在《农书》的《钱镈门》中说,他“尝见江东等处农家,皆以两手耘田,匍匐禾间,膝行而前,日曝于上,泥浸于下,诚可嗟悯”。有时候连常用的农具也不敢购置。
那么,到底田产达到多少算第一等户、多少算第二等户呢?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是以州县为单位,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规划各等民户的比例,再按比例划分户等,从富到贫,划完一等划二等;加之分别按田地、浮财或“家业钱”数计算,划分起来更难一致,往往是各地自己掌握,“随其风俗,各有不同。或以税钱贯百,或以地之顷亩,或以家之税财,或以田之受种,立为五等。就其五等而言,颇有不均,盖有税钱一贯或占田一顷,或积财一千贯,或受种一十石为第一等;而税钱至于十贯,占田至于十顷,积财至于万贯,占田至于十顷,积财至于万贯,受种至于百石,亦为第一等”[23],这就更增加了乡间小吏籍查各家财产的时候做手脚的空间,增加了划分户等的混乱程度,也增加了中下层农民家庭的生活压力和艰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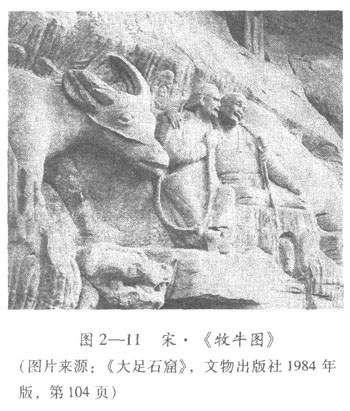
不过,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等民户之间的比例还是有一个大致的标准的。北宋初到南宋末各地区主户与客户的比例均为65:35,就是说乡村中一直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没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完全靠当佃农、雇工为生。这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比例数,因为通常讲古代包括宋代的租佃关系的时候总是夸大,把租佃关系说成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关系,有的宋人文集讲某一地区茫茫村落间都是佃户,其实佃户所占的比例仅为三分之一,将近三分之二的农村家庭属于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近年来已经有学者认识到自耕农才是古代乡村社会的主体,这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至于主户中各等户的比例,从一些片断记载和近人的论著中也可以窥见其大致情况,即上等户(一二等户)最少,中户(三等户)的数量居中,下等户(四五等户)最多,呈金字塔形。可征引几条记述: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六之一六九栽乾兴元年(1022)有上封者言:“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算,中等以上可任差遣者得千户。”是上中户占三分之一,下户占三分之二。
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一载,“逐县五等版籍,中等以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第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同书卷二六叉说:“万户之邑,大约三等以上户不满千……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是中上户占十分之一.下户占十分之九。
《宋会要辑稿·瑞异》三八之八载,乾道三年(1167)临安闹水灾,在280户中仍然可以承担税役的上户45家,其余235家为中下户。是上户占主户的二十分之一。
石介《徂徕集》卷一载,南宋初年严州主户共82197丁,其中第一至第四等户家庭的丁数为10718,第五等户家庭有丁71479,“十分之中九分以上尩瘠困迫,无所从出”。第五等户家庭占了将近十分之五。
范成大《昊郡志》卷十九估算苏州五县征发挖河役夫的时候说,“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万户,自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户”,是中上户只占百分之三。
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第一章计算出,下户占宋代总户数(包括客户)的43.3%至58.5%。
……
在当时还有一些笼统的说法,譬如“上户居其一,下户居其九”之类,都反映出乡村中的下户家庭多,上户家庭很少的事实。上户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相当于地主(最近有学者称之为“富民”)阶层,这个阶层在历代都不会超过十分之一;中下户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加上佃农客户家庭,占了乡村家庭的十分之九以上。
我们前面提到乡村农家的经济阶层明朗化了,在此可以再补充说明一下。宋代的乡村主户五等户与此前的户等制度一样,都是为了征派税役而划分,都是依据资产和人丁的多少。问题在于,此前的三等或九等划分或者过于简单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或者过分细碎而使界限模糊,更重要的是,都是只按资产的多少而没有出现资产的有无这个重要界限,远不如主客户基础上的五等划分更接近乡村农民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当然,五等户的划分与阶级的划分相比仍然显得细碎,却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已经接近阶级的划分了。打通我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来看,宋代是农村阶级关系定型的时期,以前由于门阀世族和奴婢的大量存在,阶级结构更为复杂。宋代以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村中的阶级关系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直到近代还是这样。20世纪上半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划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列举的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和赤贫等阶层,完全可以在宋代乡村中看到,甚至有的称谓都是相同的。这说明,宋代的乡村五等户制度尽管立制的本意只是为了便于征派赋税徭役,客观上却是对当时乡村农家经济阶层的精确划分和记录。
宋代官府把乡村农民家庭划分为主户客户,又把主户划分为五等,当然不是为了确定家庭经济阶层,而是为了更方便地征派各种赋税徭役。为了根据各家的贫富状况征发不同的税役,特别是各种徭役,宋代还专门把徭役划分为若干种类,让一无所有的客户家庭承担修河筑路之类的普通力役;主户中的上户家庭负担相当于乡间小吏的里正、户长以及运送官物的衙前;中下户家庭负担普通的乡间事务,如乡兵性质的弓手、壮丁和官府的手力、承符、承帖之类的差役,最下等的五等户家庭中的男劳动力也要到地方衙门去做杂职差事。与当时的各种赋税相比,徭役是比较繁重的,所以当时的人就说“但闻有因役破产者,不闻因税破产者”。[24]特别是充当衙前、里正这种差事,经常需要自己垫赔,家里没有资产是不能承担的。像浮梁县一个叫臧有金的土财主,是当地一霸,就是不输租税,在门外种了很多柚子树,让催税的人难以靠近,还在各个门口拴上10多条恶狗,里正们都不敢上门收税,“每岁里正常代之输租”。[25]长沙县有些大户不肯输租,加上一些中下户家庭因缴不起租而逃亡,全靠里正垫赔,里正推给了户长,结果“所差户长辄逃去”了。[26]还有前面提到的有的家庭为了降低自家的户等,不充任衙前、里正,甚至让寡母改嫁,或非命求死。中下户的负担也是很沉重的,而且越到中下户家庭,所负担的徭役的名称越多越混乱,往往弄得他们倾家荡产。
注释:
[1]《文苑英华》卷七四六。
[2]胡宏:《武峰集》卷二。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
[4]李元弼:《作邑自箴》卷四《处己》。③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一。
[6]《宋史》卷–/k五《食货志》。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原注:或坊郭家产及五千缗,乡村及二千缗养一匹。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卷三九二、卷四七三。
[11]《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六。
[12]李元弼:《作邑自箴》卷八《状式》。
[13]参见邢铁:《户等制度史纲》,第4页。
[14]《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八六。
[15]《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一○。
[16]《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六之二三。
[17]郑獬:《郧溪集》卷十二。
[18]《宋文鉴》卷四七。
[19]《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十;《宋会要辑稿·食货》七0之八九:
[20]《宋史》卷三一一《吕公绰传》。
[21]《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
[22]《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考》。
[23]《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二四。
[24]《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五。
[26]《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