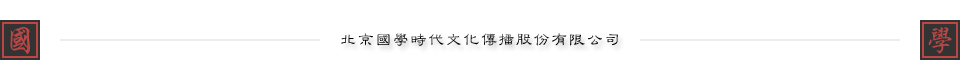关于[隋唐五代]分家析产若干类型分析——《中国家庭史》第二卷第四章第三节
二、联合家庭兄弟分家模式
父亲生前没有立遗嘱,死后若干年内尚没有分家,形成联合家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离心因素,兄弟之间要订立契约分家。敦煌文书斯4374号《分书(样式)》就是适合这种情况的一个样本[1]:
兄某告弟某甲□□(累叶)忠孝,千代同居。今时浅狭,难立始终。□□(恐后)子孙乖角,不守父条。或有兄弟参商,不□(识)大体。既欲分荆截树,难制颓波,□领分原,任从来意。家资产业,对面分张;地舍园林,人收半分。分枝各别,具执文凭,不许他年更相斗讼。乡原体例,今亦同尘,反目憎嫌,仍须禁制。骨肉情分,汝勿违之。兄友弟恭,尤须转厚。今对六亲商量底定,始立分书,既无偏坡(颇),将为后验。人各一本,不许重论。
某物 某物 某物 某物 某物
车牛 羊驼马 驼畜 奴婢
庄园 舍宅 田地乡籍 渠道四至
右件家产并以平量,更无偏党丝发差殊。如立分书之后,更有喧悖,请科重罪,名目入官,虚者伏法。
年 月 日
亲见
亲见
亲见
兄
□
□
妹
这份样文分为五部分。一是签订契约的缘起,这里着重强调兄弟本来和睦相处,同居共活,但是,如今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为了防止日后子孙纷争,乃实行兄弟分家。二是强调分家的原则是要均平、要和气。所谓:“家资产业,对面分张;地舍园林,人收半分。分枝各别,具执文凭,不许他年更相斗讼。乡原体例,今亦同尘,反目憎嫌,仍须禁制。骨肉情分,汝勿违之。兄友弟恭,尤须转厚。”三是关于家庭财产的分割内容。四是关于违反分家契约的处罚:“如立分书之后,更有喧悖,请科重罪,名目入官,虚者伏法。”五是分家契约签订的见证人和当事人的签名。
这是一份父亲去世若干年后兄弟分家签订契约的样本。许多家庭在父亲生前和去世后若干年,兄弟之间都没有立即分家,而是在一起过日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分家的事也是很常见现象,这份契约文本就是为这样的情况准备的,说明在当时也很常见。我们在敦煌的一些借贷文书中发现兄弟借贷的责任关系文书,可以窥见兄弟之间经济关系之一斑。如伯3458号文书《辛丑年(941)四月三日罗贤信贷生绢契》:罗贤信从范庆住那里借得生绢一匹,规定将来要还本利两匹,就要借贷人的弟弟罗恒恒承担还贷责任。[2]又如伯3472号文书《戊申年(948)徐富通欠绢契》[3]:
戊申年四月十六日,兵马使徐富通往于西州充使,所有些些小事,兄弟三人对面商议,其富通觅官职之时,招邓上座绢,恩择还纳,更欠他邓上座绢价叁匹半。或富通身东西,仰兄富庆弟盈达等二人面填还,更不许道说东西。恐后无信,故立此契,用为后定。
兄富庆(押)
弟盈达(押)
见人弟富住(押)
这里明确提到,徐富通在到西州出使之前,就他本人几年前所借债务的偿还问题,与兄富庆和弟弟盈达三人面对面地进行了商议,因而订立了这个担保性的契约。其中另外一位弟弟富住只是以见人(证人)的身份出现,说明这份契约除了满足债主邓上座之外,还是要约束两位兄弟承担还债义务的。我推测这兄弟三人可能并没有分家。伯3004号文书《乙巳年(945年)徐富通欠绢契》[4]就是三年前徐富通向邓上座借贷的契约文本,当时签名的人是:
还绢人兵马使徐富通知
还人徐富庆同知
还绢人弟徐盈达知
见人索流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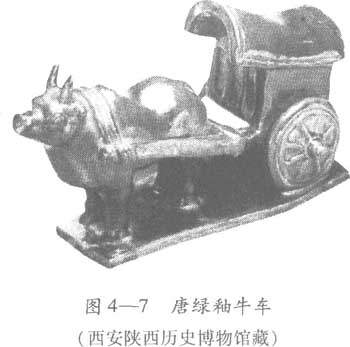
这里兄弟三人都有签名,“见人”是非本家兄弟,说明是与邓上座签订的契约,而前面那个契约则是邓上座担心徐富通万一死亡或者不回,借贷出去的绢无法收回而要求兄弟间签订的契约。这类情况的出现表明,尽管兄弟之间没有分家,但是,在债务偿还问题上,人们还是担心出现偿还信誉和义务上的法律漏洞。即使在父债子还的场合,有时候也要将契约加以约束。如斯5632号文书《辛酉年(961)陈银山贷绢契》[5]:陈宝山向弟弟僧银坚借贷绢一匹,“其绢限至来年九月一日填还本绢。若是宝山(当即陈银山)身东西不在者,一仰口承人男富长祗当,于尺数还本绢者。”签字画押的人分别是:贷绢人男富长、贷绢人兄陈银山[6]、知见人兵马使陈流信。这是兄弟之间的借贷,借贷一年并没有说利息,只说要还本钱。大约是因为兄弟的关系。正因为是兄弟之间,所以要求儿子在父亲不能偿还的情况下,要替父亲还给作为出贷人的叔叔。还有3565号《甲子年(904或964)汜怀通兄弟贷生绢契》[7]也是兄弟共同借贷:“当巷汜怀通兄弟等,家内欠少匹白(帛),遂于李法律面上贷白生绢壹匹”,当年秋天要还利息麦四石,次年二月再还本绢。若到时还不能还,另外“于看乡元逐月生利”。这里的借贷主体是兄弟四人,签字画押的也是四人:“贷绢人文达、贷绢人怀达、贷绢人怀住、贷绢人兄怀通。”这里借贷的四兄弟显然没有分家,所以他们共同承担借贷还贷的责任和义务。[8]
敦煌文书斯4489号背记载了慈惠乡百姓张再通与房兄富通的财产纠葛。[9]张再通上诉早年被房兄张富通卖身给贾丑子,得绢六匹。其钱全部被兄富通拿走,“再通寸尺不见”。几年过去后,再通仍然是穷光棍(单贫),回到甘州,想“收赎本身,诤(争)论父祖地水、屋舍”。这些显然都是在没有分家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兄富通可能已经死亡,而“其养男贺通子不肯割与再通分料舍地”。而兄张富通先前又“广作债负,买(卖?)却再通所有父祖地水,不割支分”。这里有误字(文书另一处已经把买与卖写错),大约是指张富通卖掉了再通父祖的耕地,不留一点给再通。现在债主早晚催逼还债,再通无法,请求官府做主,要富通的养子来还卖身钱和父祖的土地房屋。这个案子其实还是涉及财产分割和吞并问题,养子要承担债务问题,还有卖身、赎身问题。根据前引唐朝律令,儿子分家另过三年、逃走六年就不得参与家庭财产分割,除非有父祖遗产在内。现在富通把父祖的田产卖掉,使再通无法继承。但是,留下的债务却要再通还债。这自然是极其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再通要求富通的养子来偿还债务。
还有一件文书涉及兄弟间的债务分担问题。伯3501号背(6)的内容是[10],后周显德五年(958),百姓王员定提出:员定、员奴、员集兄弟三人虽是同父母的兄弟,但是,由于家里贫穷,各人都在外边营生(“三个与人边寄贷”)。现在,员奴、员定已经“口承新乡”,即落户到新的地方去了。三人的债负已经分割完毕,其余剩下的债务由员定来负责偿还,作为报偿,员定得到房舍一间、城外园舍地三亩,为了不使员奴、员集今后来要这份产业,员定请求官府给一个凭判。我们无法判定这些兄弟是否同籍还是异籍,显然他们在父母死亡时并没有分家是可以判定的。只是在员定、员奴已经到新的地方落户,自然分家之后,他们涉及处理共同的父祖遗产和债务问题。
斯4654号背也有一个关于兄弟债务问题的文书。[11]慈惠乡王盈子、王盈君、王盈进、王通儿四人是同胎共气的胞兄弟,父母去世后分家。“所有父母居产田庄屋舍四人各支分,弟盈进共兄盈君一处同活”。不久盈进身患重病,数月而亡。可是盈进却在当年当着重役。由于无人承当,就被当做流户看待。流户的“役价”无法填还,应由同居之户承担。现在的问题是,盈进生病时本来就欠了很多债务,这些债务都由盈君在承担。而盈进本来只分了城外七亩土地,房舍一间,“城内有舍(缺),况与兄盈君□□□取填还债负如后”。这里有缺文,详细内容不得而知。大体是希望减免盈进所承担的重役的“役价”,为此特把盈进和盈君所负担的债务负担开列如后。盈进与盈君两兄弟“一处同活”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值得在这里探讨。实际上是兄弟四人分家,但是老二和老三仍然同居一室,合为一个居住户。这里的情况显然比较清楚,那就是已经分家的兄弟,他们各个偿还个人的债务。而此处所涉及的债务,原则上说只是盈进本人的债务,但是由于同居共活的关系,盈君难免被牵扯进去。他要求卖掉弟弟的财产偿还债务。可是大哥盈子似乎不同意。我们可以设想,此处盈进显然没有家室,他死后便成了绝户,绝户的财产是可以有近亲收管的,只要盈进没有遗嘱给盈君,那么财产就可以几个兄弟共同瓜分。这也许就是盈子不同意轻易卖掉弟弟财产的意图所在。
注释:
[1]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185~186页。
[2]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119页。
[3]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123页;沙知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也收录此件文书,“富通”识为“留通”,“富庆”识为“留庆”,“富住”作“留伍”。
[4]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122页。
[5]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127页。
[6]此处的贷绢人“兄”是从出贷人的身份讲的。陈银山为出贷人僧银坚之兄。
[7]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128页。
[8]在敦煌的许多举钱契约中,借债人往往举家签字画押,例如《建中三年(782)马令痣举钱契》的签字人在“钱主”后相继是:“举钱人马令痣年廿,同取人母苑二娘年五十,同取人妹马二娘年十二。”(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140页)表明这些签字画押人员都是借贷家庭的成员。
[9]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307页。
[10]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303页。
[11]唐耕耦、陆宏基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