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唐五代]家庭财产析分的若干问题——《中国家庭史》第二卷第四章第一节
第四章 家庭财产的析分
第一节 关于家庭财产析分的若干问题
我们在分析家庭结构的时候,曾经指出三代是否同居是一个关键概念。换句话说,父母在,成年兄弟结婚生子后是否分家,是判定家庭结构的关键所在。从家庭生活上说,成年兄弟结婚之后是否仍然在一起生活,最大的变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成年兄弟已经有自己的经济收入或者比较独立的劳动能力,不再完全倚赖于父亲,从而产生离心倾向;另一个是兄弟结婚后,在家庭引进了非血缘关系的成员,这个成员只是与婚姻当事人有休戚与共的亲缘关系,与其他家庭成员反而处在一种竞争关系,比如妯娣之间就是最难相处的关系,媳妇进门后儿子最亲密的人是老婆,从而使从小受父母庇护的儿子与父母产生了距离,尤其会使婆婆难过,于是婆媳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也很难处。总之,这些因素导致兄弟成婚后维持大家有相当难度。而从唐朝的国家政策来说,禁止父母在世的时候兄弟分家。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于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法律对于同籍异财又网开一面,有所谓“但云同籍,不言异财”的补充说法。这就使家和户的内容发生了背离,使分家也有了不同的意义。
一、分家的双重含义
人们一般把家庭定义为以婚姻前提下的血亲或者姻亲关系为基础的、同居共爨的生活单元和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在家庭的这些构成要素中,婚姻前提下的血亲或姻亲关系是基础,同居共财的生活单元是实质,而作为社会组织的外显形式则是户籍。虽然有些家庭并不同时具备这三种要素,也可以看成是它的变态形式。[1]在诸种要素之中,财产的共有关系乃是家庭最本质的关系。“同居共爨”的真正意义,主要是看家庭成员在财产上是否有统一的收支方式,而不是指他们形式上是否有统一的居住空间。特别是在中古时代二元制家庭结构中,判断那些具有血缘或亲缘关系的人们是否构成一个家庭,关键是看他们是否共财,而非同籍。于是,我们所谓的家庭析分就首先是指财产的析分,然后才是户籍的分开。下面我们结合唐代的法律来分析这个问题。

完整意义上的分家,应该包括获得独立的户籍(别籍)和获得独立的财产会计(异财)两个内容。《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律》“子孙别籍异财”条云:“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疏议云:“若祖父母、父母处分,令子孙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得徒二年,子孙不坐。但云‘别籍’,不云‘令其异财’,令异财者,明其无罪。”[2]这条法律说明,一个家庭若不改变户籍的登记形式(别籍),祖父母、父母做主为子孙分割家产,即“同籍异财”是合法的。因此,父母主持下的“同籍异财”,是常见的家产析分方式。别籍是一种政治上和行政上的权利获得,异财是一种经济上和财政上的权利获得。别籍说明析分的小家庭得到官府的承认;异财说明析分的小家庭创造的财富再也不需要汇入大家庭之中,小家庭成为独立的经济核算单元。可见异财的决定是一个家庭的家长自己就可以作出的;别籍的操作并不由家长自己决定,家长决定了还要被判刑。异财可以是很隐蔽的,别籍则是一种很公开的行为。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唐代的法令是严格限制百姓别籍异居的,违者被处以徒刑;但是又不立法处分同籍而实际异财的家庭。正是这种法律上的运作空间,使得实分名不分的家庭析分现象在唐代层出不穷,从而出现各种“二元式”家庭结构。
同卷《户婚律》“相冒合户”条还规定“诸相冒合户者,徒二年,……即于法应刖立户而不听别,应合户而不听合者,主司杖一百”,疏议曰:“应别,谓父母终亡,服纪已阕,兄弟欲别者。”由此规定可见,只要父母尊长去世,而且居丧期已过,每一个兄弟都有权向官府提出别籍的要求,分立户头。这说明只要父母尊长亡故,兄弟或者媳妇中间,只要有人要求另过,分家就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合法行为。
根据这样两种法律,分家就有了民间和官方的两重意义。从民间来说,异财就已经是分家,从官方来说,只有别籍才承认是分家。在敦煌文献中甚至还出现了强令与尊亲合贯的事情,说明国家对于父母在而别籍的禁止是非常严厉的。[3]国家默认财产上的分家,而拒绝户籍上的分家,于是分家的行为被从经济关系和政治(行政管理)关系两个层面割裂了。
这样官方和民间两种分家行为的过渡关系,在唐代户籍中的三状注记中有所表露。所谓三状注记是指该户籍的户主往后逆推三代户主,但是不包括居丧期问分开的临时户主。唐代一般老百姓中,在父亲去世后,因为没有了法律的障碍,兄弟同时分家,于是每个兄弟都成为分家后的新户主。但是,在居丧期间和正式分开之前的两年中(唐律规定,丧服期内不得分家),户籍上的户主就是长兄,其他兄弟都在此户贯下。[4]而在实际上,这些兄弟未必只是在父母去世那一天才分家,也许早就已经异财分爨了。父亲生前也不过是名义上的户主,但死后连这个名义也不可能,于是长兄成为过渡时期的户主。分家也就从过去的“异财”发展到“异籍”的阶段。
二、家长的权力与财产归属
家长一词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出现。[5]唐朝法令一般称为尊长但尊长是一个复数,包括父母祖父母,而家长则只有一人,一般就是户主,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令:“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6]这里的家长与户主的分别,其实就是对于家庭的两种定位的分别,家长是作为一个血缘婚姻单元的首长,户主是作为一个社会基层组织的首长。法律认为,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人。
关于家长的权力,日本学者仁井田陞认为有四个方面,即申告户口;输纳租税;不得荒芜田畴;家人犯罪时的连坐责任。[7]此外,王玉波等也对此有专门的讨论。[8]高明士总结诸家观点,提出唐朝法律规定的家长或户主的责任是:祭祀祖先;教养子孙;申告户口;输纳租税;主婚权与责任;家人共犯而独坐家长的责任。[9]以上这些讨论都没有涉及家长对家庭财产的处理权问题。[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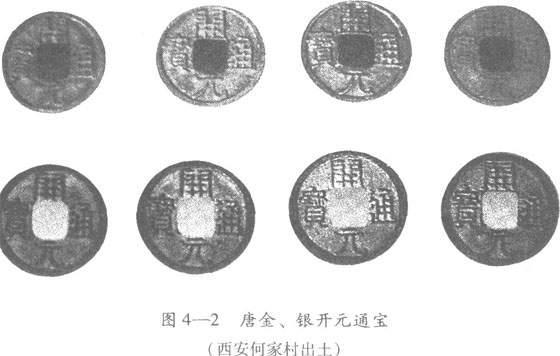
一般印象认为家长是家庭事务的主宰,包括财产的处置在内。日本学者则有分歧的意见。究竟是家族共产,还是家长独自拥有财产权,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包括中田薰)与滋贺秀三各有不同看法。仁井田陞和中田薰都从父家长权威去解释父亲的财产处理权,中田还另外加了父亲的教令权的概念。[11]滋贺秀三与之不同,他强调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家庭成员是共同拥有全部家庭财产,或者对如何处置家庭财产具有发言权,但是,从法律意义上说,只有男性长辈家长拥有独立地处置家庭财产的权力。滋贺秀三特别强调作为家长的父辈在处理财产文书上的签字权。只要父亲签字而无需儿子连署,这说明财产属于父亲所有。[12]此外,从家庭负债的角度说,儿子负债只有在父亲默许的情况下才可以成为家庭的债务,而父亲的债务儿子却必须无条件地偿还。[13]尽管父亲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是否分家以及给自己预留多少养老份额,但是却无法改变诸子财产均分这样的事实。即使是有父亲的遗嘱,在分配财产上也不能有随意性。滋贺秀三解释说,由于中国人有父子一体的观念,认为家庭的传承表现为祖先和子孙的连续关系,家庭的生命就是通过男性子孙的血脉延续来完成的,财产继承只是这个传续过程的一个方面。[14]
从法律的原理层面说,滋贺秀三的分析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它是剥离了各个具体情形后所进行的纯粹的理论分析。但是缺陷也正在于此,这个理论既缺乏历史感又缺乏现实性。历史上中国家庭的财产关系并不完全符合这个原理,就本卷要讨论的隋唐五代的情况来说,滋贺秀三所举的那些例子几乎是不适合的,我们在敦煌借贷和债务文书中就发现家长与家庭成员同时签名的例子。[15]在现实中家长在处理财产时绝大多数场合并非不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也力求处分公允,所谓“一碗水端平”。但是,这与家长是否拥有绝对的财产处置权毕竟不同。唐初功臣刘弘基于永徽元年(651)卒,“弘基遗令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顷。谓所亲曰:‘若贤,固不藉多财;不贤,守此可以免饥冻。’余财悉以散施”[16]。刘弘基并没有把家庭财产全部处分给儿子,而是散施给外人。可见家长处分财产的权力是独立于其财产继承人的意志的。[17]即使其他家庭成员判断,家长在某个家庭财产处置行为上会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其他家庭成员除了劝告外,并无有效的法律手段加以阻拦。相反,卑幼则不经家长许可无权随意处置家庭财产。《唐律疏议》对此的规范是:“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18]
三、国家政策与民间风俗
关于隋唐五代时期国家的家庭政策(或称家族法)已经有学者进行过细致的考察,一些基本史料都已经做了梳理。[19]大致说来,隋朝和唐朝以及五代都从正面评价累世同居的家庭模式。从实际操作层面上说,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的。
隋文帝开皇年间进行大规模户口调查:“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20]这种政策是针对当时的户15不实的情况而施行的。因为山东自北齐以来大量户口隐漏、丁口不实,影响了赋役征发,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隋文帝下令大规模“貌阅”,特别是将大家族析分,一个家族之中,大功以下亲属,即属同一祖父的堂兄弟,必须另外建立户籍。结果新增人口164万余人,其中的丁男多达44万余人。这虽然纠正了当时户籍中隐瞒丁口的情况,但是,却是与国家一贯推行的奖励大家族同居的政策相矛盾的。因此,我们倾向认为隋文帝在统一后在北方地区大力推行户口调查,甚至不惜强令大功之家析籍,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说隋朝鼓励小家庭模式。
从社会风俗习惯上说,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盛行大家族制度。[21]南方地区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说到南朝的家庭状况:“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其问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先有善于家者,即务其赏,自今不改,则没其财。”可见,南方的家庭析分无论在上层还是下层都是相当普遍的。小家庭结构在整个家庭结构中占到了“十家而七”、“八家而五”的比重。
南朝末年,北齐卢思道出使陈朝,酒席间宾主联句作诗。卢思道讽刺南方分家之俗说:“‘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为南人无情义,同炊异馔也。”据说,卢思道的句子使“吴人甚愧之”。[22]吴人是否甚愧之,还不好说。但是这个例子却说明南方许多人家分财却未必分居。也就是还在一个厨房里做饭,但是,饭菜却是分开做。当然肯定还是住在一个屋檐下了。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住房的限制,即兄弟乃至父子之间虽然分家了,但是迫于经济条件还没有办法使其中的一家搬出去住。二是国家政策的限制,即国家政策不允许父母在而成年儿子分家另过,因此不得不保持一个家庭的形式外壳。
南方这些小家庭之间并不排斥互相救助。例如《魏书》卷七十一《裴叔业附从子植传》云:裴“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这样一种兄弟分家过日子,但仍然奉养老母、赡及兄弟的做法被士大夫目为“江南之俗”,可见当时北方确实是另外一种风俗。[23]裴植传后面还有一句话:“植母既老,身又长嫡,其临州也,妻子随去,分违数岁,论者讥焉。”从这个话里面可以看出,士大夫之家的嫡长子为官,要么应该把老母接去同住,如果母亲愿意留在乡下,至少应该把妻子留在母亲身边侍养。否则,就会受到舆论的批评。河东裴氏是北方著名士族,裴叔业归魏前,祖父三代仕于南朝,难免入乡随俗,在家庭的组建方式上受到了南方的影响。

唐代民间诗人王梵志的诗歌以写实著称。他一方面说:“兄弟相怜爱,同生莫异居。”“兄弟须和顺,叔侄莫轻欺。财物同箱柜,房中莫蓄私。”[24]可见他是不主张兄弟分居异财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细致地观察到:“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元(原)来心里喜。”[25]从这样比较矛盾的材料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心理于一斑:从社会舆论上说,大家都主张兄弟叔侄应该和睦不分家,但是,即使在父母在世之日,成年兄弟已经在巴望分家另过了,所以“口哭原来心里喜”。如此说来,南北朝时期分家析产还只是风行南方,到了唐代也成为北方居民的普遍诉求了。
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还能做什么呢?唐朝官府一贯通过旌表的手段来鼓励民间数代同居,有时候还给予实质性的奖励。例如开成三年(838)十一月,“户部侍郎李珏奏庐州舒城县太平乡百姓徐行周,叔伯兄弟五代同居,请免其同籍户税,从之”;后唐末帝曾经颁令对镇州和晋州的许多乡里予以旌表,用“仁孝乡”、“旌义里”、“敦俗乡”等命名了那些产生累世同居的孝义人家的地方,还“版署文参之名”(即授予一个名誉官衔)。[26]又是减免税收又是授予官职,目的就是敦励风俗,建立一道阻止分家析产的道德堤防。
综合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隋唐时代总的政策仍然是鼓励同居共籍的大家庭,除了隋代初年一度为了防止大户包荫而在户口检查中命令三代同居家庭(大功以下)析户外,唐朝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下令父母在而析户的家庭要与尊亲合贯。从民间实际的家庭生活模式来看,南朝时期“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和“庶人父子异产”的情况可能是相当普遍的,而《唐律疏议》中的法律条文不过是对这种状况的认可罢了。
四、虚假的分家与合户
国家对于民间户籍的分与合有一定的政策,民间也有通过改变家庭户口形式而谋求经济利益的。一般来说,普通老百姓要钻国家政策的空子,以便通过变更家庭户口形式来获得赋税上的好处,通常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合户”,另外一种办法是“分家”。

唐朝法律是禁止“相冒合户”的:“诸相冒合户者,徒二年;无课役者,减二等。”疏议解释:“既为同居有所蠲免,相冒合户,故得徒二年。无课役者,或籍资荫赎罪,事既轻于课役,故减二等,得徒一年。注云:‘谓以疏为亲’,律令所荫,各有等差,若以疏相合,即失户数;规其资荫,即失课役。如斯合户,得此徒刑。”[27]这条律疏实际谈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普通家庭为了逃避赋役,通过以疏为亲的办法把本来是两家合为一户,从而获得蠲免上的好处。另外一种情况是那些本来没有课役的官宦人家,通过合并两家为一户,从而获得刑罚减免上的待遇。
至于通过分家来获得赋役上的好处主要是因为唐朝前期实行“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的差科派役政策,[28]富室多丁之家户等也高,那么分家可以减少家庭的丁口和财产的数额,从而可以减少或逃避差课。为了防犯这种情况泛滥危及国家赋役,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七月二十三日敕云:“天下百姓,父母令外继别籍者,所析之户等第,并须与本户同,不得降下。其应入役者,共计本户丁、中,用为等级,不得以析生蠲免。其差科各从析户祗承,勿容递相影护。”[29]这则敕文的针对性很强。它要求因为外出继承绝户而分家析出之户,要与分家之前的户等相同,不得因析分而降下,分派差役也不得因析户而人丁的减少有所减免。即户等的确定、丁中役事的分派都要按照分家之前的状态进行。可见国家一方面关注的是分家析户引发的国家赋役的变化,另一方面大约也是为了惩戒无端分家者,让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但是从效果上看,似乎并不很明显,未必能完全解决民间分家析户的趋势。所以,唐玄宗一再发出禁令,甚至不惜以刑罚相威胁。[30]其实际效果很有限。
唐代后期实行两税法,赋役征收原则及户籍制度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上疏建议实行两税法,“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然两税法仍保留了原来三年造籍的旧制,“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31],但徭役征发不再以人丁为本,而“唯以资产为宗”,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也就是说原则上家庭财产成为赋役征发的主要根据。陆贽对于这一点是抱有相当的保留态度的。他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家庭财产的确认上:“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囤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32]我们可以想象,理论上说,家庭财产的分割应该是有利于降低纳税基数的。
也有人认为两税法实行后以户口的增殖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做法,直接导致了析户之风的盛行。宪宗元和六年(811)二月制文指出:“自定两税以来,刺史以户口增减为其殿最,故有析户以张虚数,或分产以系户名,兼招引浮客,用为增益。至于税额,一无所加。”[33]从这里可以看出,分家析产并不会给官府带来更多的赋税收益,却会给地方官带来管内户口数增加的虚名。我们还无法完全判断地方官会强制老百姓分家析产,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他们对于民间的自然分家应该不会采取强烈阻止的立场。官府处心积虑建筑的道德堤防也就加速崩溃了。
注释:
[1]例如,收养关系的家庭是拟制的血亲关系;因为求学、经商或者出仕,而不能同居共爨的家庭,其实是财产共有的。
[2]《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律》,第236页。
[3]敦煌所出《唐开元十年(722)沙州敦煌县玄泉乡籍》有“开元七年籍后被其年十二月十三日符从尊亲合贯附”等字样。池田温解释说:合贯“即将籍贯合并为一”。参见[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中国占代籍帐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3页。
[4][日]北原薰:《唐代敦煌籍的三状注记所见兄弟之间的析户和合户》,《中岛敏先生古稀记念集》上卷,(日本)汲古书院1980年版,第125—155页,此处见第136页。
[5]如《商君书·垦令》:“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墨子·天志上》:“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
[6]《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第155页。
[7][日]仁井田陞:《中国身份法史》,第417—421页。
[8]王玉波:《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l989年版,第250页。
[9]高明士:《唐律中的家长责任》,见高明士主编:《唐代身份法制研究——以唐代名例律为中心》,第40页。
[10]张中秋则认为家长的权力首先就表现在财产上。见张中秋:《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11]参见[日]中田薰:《法制史论集》第Ⅲ卷,第1331~1334页,(日本)岩波书店1943年版;[日]仁井田陞:《中国身份法史》,第450~453页。
[12]参见[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第127~132页。
[13][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第141页。
[14][日]滋贺秀三著,张建国、李力译:《中国家族法原理》,第169~179页,特别参看177页。
[15]例如,我们后面列举的敦煌文书中,家庭成员都在家庭财务契约上签字画押并不鲜见;又如父亲遗嘱在财产处理上有相当的主观因素。见《敦煌社会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所收有关文书。
[16]《旧唐书》卷五十八《刘弘基传》,第2311页。
[17][日]滋贺秀三否定家长有这种处置财产的权力,见前引书第161~165页。按《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对于“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的规定,只是适用于“兄弟均分”的场合,对于父亲的财产处分权不构成限制。
[18]《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律》,第241页。
[19]参见冻国栋:《隋唐时期的人口政策与家族法》,载《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28页。
[20]《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81页。
[21]见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载《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第1915页。
[22]《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七《卢思道》,第1915页。
[23]如果把隋文帝统一天下不久就下令按照“江南之俗”的做法强制分家析口,看成是整个国家推行“江南化”(南朝化)政策的一部分,似乎也有些求之过深。
[24]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卷四《兄弟相怜爱》、《兄弟须和顺》,第106、105页。
[25]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卷六《造作庄田犹未已》,第198页。
[26]参见《册府元龟》卷一百四十《帝王部·旌表四》,第1696、1699页。
[27]《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律》,第240~241页。
[28]《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律》“差科赋役违法”条疏议,第251页。
[29]《唐会要》卷八十五《定户等第》,第1845~1846页。
[30]《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天宝元年(742)正月一日敕文:“如闻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现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其侍丁孝假,与免差科。”(第1817页)《册府元龟》卷五十九《帝王部·兴教化》天宝三年(744)十二月制:“其有父母见在,别籍异居,亏损名教,莫斯为甚。亲殁之后,亦不得分析。自今已后,如有不孝不恭、伤财破产者,宜配隶碛西,用清风教。”(第662页)《册府元龟》卷五十九《帝王部·兴教化》肃宗乾元元年(758)四月诏:“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玷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闻奏。”(第663页)
[31]《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第1820、1818页。
[32]《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五,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4749页。
[33]《唐会要》卷八十四《杂录》,第18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