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家庭规模的总体分析——《中国家庭史》第二卷第一章第一节
四、影响家庭结构的其他因素
研究家庭规模和结构的时候还要考虑家庭的阶级或等级的差别。一般说来某个家庭人口的多寡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生理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生理因素指生育能力的强弱;社会因素指社会总体医疗水平、个人经济能力;文化因素指生育观念等(如信仰佛教的在家居士会节制性生活与生育;单传之家会特别渴望多生儿子等)。此外还应该包括政府的人LJ政策等。《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收入的一位上阳宫医博士成磷(762–830)的墓志铭,他本人虽然活了69岁,但夫人张氏早亡,留下三个儿子,在“宝历初年,相次身亡”。再娶夫人赵氏也是“少亡”,三娶夫人李氏,李氏所生的儿女也都是结婚不久就“少亡”。其家庭里夭折的人如此之多,可见比较好的医学条件,也不总是家人年寿高的决定因素。[1]
一般认为,人口政策、赋税政策会对一个时代的家庭结构产生影响。但是,从家庭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说,对于这种影响的程度也不可估计过高。比如,唐代法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在,不得别居异财。按照疏议的解释,父母可以让子女异财,但是不可以让子女别籍。实质上就是允许子女在实质上分家,但是在形式上不能分家。这里不排除政府有赋税制度上的考虑。只要不别籍,父母与子女在户籍上就是一个居民户,在户等上就不会被降低。但这也说明,政府户口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户口的形式上,而未必是家庭的结构上。由于家庭生计利益的内在驱动,农村小家庭结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但是官僚和地主家庭,一方面更重视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价值,极力维护数代同堂的大家族结构,另一方面他们在赋税缴纳方面具有合法或非法的特权,不受赋役制度的约束。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古代家庭结构的等级性差异。仁井田隍《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中国身份法史》对于敦煌户籍资料和周村十八家的人15资料已经有所讨论。[2]他注意到敦煌天宝户籍上诚如那波利贞所指出的,女口多,男口少;而周村的户口则是男口多,女口较少。他认为周末以来,中国农家的人口以5~10口为比较普遍。当然还存在着官僚和富室累世同居之家,其人口在数十口乃至数百口。这种差别应该是自古而然的。
《韩非子·五蠹》:“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是否最小的儿子结婚生子后,大父(祖父)仍未死,姑且勿论,但是,长子结婚生子后,祖父母未死的情况应该是相当平常,那么这个时候的人口便是5人。假如大父不只一个儿子,比如两男一女,那么人口就会达到6~7人。女儿出嫁后,也许第二个孙子(女)又出生了,这样家庭人口仍然是6~7人。如果第二个儿子结婚分家,则长子之家有6口,次子之家2口。假设父母与次子过,则长子之家4口,次子之家也是四口。假设祖父母辈有一位老人去世,那么剩下这位老人与长子会构成5口人,与次子暂时会构成3[J人,次子生子则亦达到4口人。这里的关键是兄弟是否分家,只要不分家,一个家庭规模很容易保持在5~10口的水平。如果按照韩非子的计算法,一家百余口也不难。《旧唐书》卷七十七《刘审礼传》:“再从同居,家无异爨,合门二百余口,人无间言。”从兄弟同居是三代,“再从同居”就是四世同堂了。史籍上类似这样一些累世同居的义门家庭,受到表彰和社会称道,恰恰证明了这种大家庭乃是罕见情形,所以才被记录下来。
仁井田隍曾推测,穷人大都在5口之下,例如北魏时:“至与老小无牛家种田七亩,老小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3]这“五口下贫家”大体说明贫穷家庭大体如此。[4]相反,一般富户多丁当至少家有5丁以上,家庭里有5个男劳动力,生产能力自然比较大,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正月赦文:“如闻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仍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5]虽然并非人口多的家庭都是富户,可就农村家庭而言,丁口多就意味着劳动力多,富户总是与多丁联系在一起是不难理解的。
家庭结构还有社会的层次性差异。第一个层次是最大多数农村家庭,统计人口在2—6口之间,实际上从单身到10口以下都属于这个层次,平均5口左右。第二个层次,一般的富裕农民和官僚家庭,家有5个以上的丁口,人口在10~20人之间。第三个层次是大官僚地主家庭,妻妾较多,子女较多,人口达到20口乃至百口。魏晋南北朝时期“客皆注家籍”虽然在唐代已经改变,但是唐代仍然有家生奴婢之类的提法。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像前举孟海仁那样将奴婢等登记于户籍之上并不鲜见。我们可以读读成书于隋朝初年的《颜氏家训》中的一段话:“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这段话被写在《止足篇》,说明是很多士大夫之家的理想状态。这样的家庭大约属于第三层次的下限和第二层次的上限之间。
表1-7 唐代家庭结构分析表
| 普通农家或城市平民家庭 | 2~6口 | 多数二代或三代 | 占绝大多数 |
| 富裕家庭或者官宦人家 | 10~20口 | 多数三代以上 | 较多 |
| 大官僚大地主家庭 | 20以上乃至百口 | 大多累世同居 | 比较少见 |
当然,实际的家庭生活毕竟不是按照平均数来安排的。现实生活中,家庭人口的结构可以说千差万别,甚至往往严重偏离这个“基本数据”。这里首先是贫穷农家和富贵人家的人口结构和子女数目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假如我们以2~6口之家作为农村家庭结构的基本形式的话,则家庭结构有如下模式:
两口之家:母子;夫妻
三口之家:夫妻、子女一;夫妻或父母一;夫妻或弟妹一
四口之家:夫妻加子女;夫妻加父母;夫妻加子女一、父母一;夫妻加父母一、弟妹一
五、六口之家:夫妻加子女;夫妻加父母、子女;夫妻加父母、弟妹;夫妻加弟妹。
丁口在5丁以上的富裕家庭或者官僚家庭,其人口结构的主要差异是成年兄弟仍然同居共爨。
总结以上模式,两三口之家,不大可能有三代结构。四口之家,如果是三代结构,最多只能有一个小孩(如果妻子死亡,亦当续弦)。五六口之家的家庭结构模式就比较多样化了。但是,三代的结构也限制了孩子只能有2—3人。如果我们以两个子女为普遍情况,4、5口为一般家庭结构模式的话,说明唐代大多数贫民家庭是两代人,三代共居者当很少。但是,人口在10人以上的官僚地主家庭则大多有成年兄弟同居的情况,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一是儒家礼法文化的影响。士大夫之家大多是儒家文化的倡导者,我们看到许多唐朝讲究礼法门风的家庭,都追求大家庭生活模式。《新唐书》卷一三o《裴漼传》:从祖弟“宽兄弟八人,皆擢明经,任台、省、州刺史。雅性友爱,于东都治第,八院相对,甥侄亦有名称,常击鼓会饭。”兄弟八院相对,构成八房小家,又常击鼓会饭,有共爨同居之意,构成一个大家。
二是经济基础的雄厚。官宦人家和富裕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可以有条件支持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唐代官员70致仕,官宦之家的家长往往越是年长职位也高,在社会上的地位高,对于家庭的影响力也比较大。相反农村家庭,父亲年老后体力衰迈,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是年轻人,整个家庭的凝聚力也随着家长控制力的减弱而弱化。
三是职业特点。官宦人家的子弟大多追求功名,弱冠之年正在读书赶考的时候,出仕之后由于在外地做官,在客观上使大家庭难处的诸多因素都获得了缓解。因为离开了老家,所以实质上成了同籍异财的家庭形态。当老家长去世后,这些官宦人家也就自然在各地建立自己的新家业,决不会回去再与兄弟同居,就像现代社会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刚开始还常去看望老父母,结婚以后特别是家乡的父母去世后就自然分家了。为此,我们举一个城南杜氏家族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杜牧的从叔杜诠并不足一个很热衷功名的人,但是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官,使他得以祖父之荫出仕扬州参军,后来出任江夏县令,罢任后就在南方定居。“自罢江夏令,卜居于汉北泗水上”。[6]杜诠后来还曾为复州司马,只做了半年就弃官而去。但是,这些北方土族虽然在南方安家置业,死后却大都想归葬于老家。在杜诠的场合就是终于汉上别业,却葬于长安少陵。我们不清楚杜诠是如何从他的大家庭分离出来的。但是在南方定居应该是重要原因。杜诠在出来做官以前,与老家的大家庭一起生活,颇得祖父疼爱,据说其祖父的家庭,“富贵繁大,儿孙二十余人,晨昏起居,同堂环侍。公为之亲,不以进。门内家事,条治裁酌,
图1-3 雨中耕作图(敦煌石窟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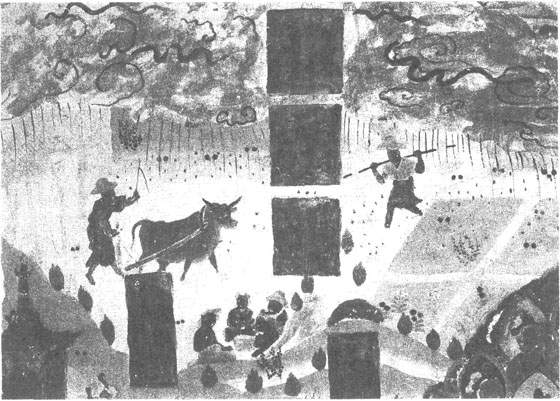
至于筐箧细碎,悉归于公,称谨而治。”[7]杜诠的父辈在外地做官,像他这样的孙辈留在老家,与祖父生活在一起。在祖父的大家庭里杜诠是一个管家的角色,所以迟迟没有出去做事。后来之所以入仕,估计与祖父母去世有关。入仕后,杜诠当与原来的家庭渐行渐远。门荫人仕在唐代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杜诠对仕途也不感兴趣。他罢江夏县令后卜居于汉北泗水之上,显然还有其他原因。估计此时杜诠已经自然与原来的大家庭分家,他即使回去也没有资产屋舍可以继承,而南方正在开发之中。杜诠做官的收入是极为有限的,不足以使他在北方再添置什么产业,而分家的财产和做官时正当非正当的收入,却足以资助他在江汉垦荒。他“烈日笠首,自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两余,三年而室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于垦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完全建立了一个新的家业。
我们这里当然主要不是讨论分家问题,我们只是探讨杜诠从他出身的那个大家庭析分出来的过程。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三代同居的家庭结构问题。
总之,根据我们以上分析,官宦人家三代同居的家庭结构比较多,有其客观原因。农民家庭父母在而实质性分家的恐怕占有多数,也是由其经济生活的特点决定的。
注释:
[1]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1,第904页。
[2][日]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书研究》,(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744-755页;《中国身份法史》,第352~359页。
[3]《通典》卷一《食货一·田制上》。
[4]参见[日]仁井田陞:《中国身份法史》,第338—339页。
[5]《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
[6]杜牧:《唐故复州司马杜公墓志铭并序》,载《樊川文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l41页。本段下文引此不另出注。
[7]关于唐代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内部治理情况,订立于唐末大顺元年(890)的《江州陈氏义门家法》规定得颇为详尽,可参见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2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