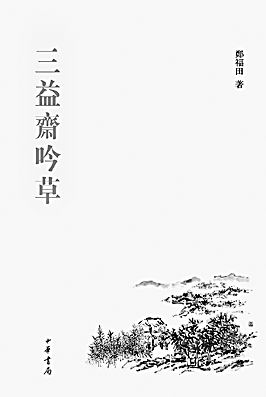最是一年春好处
近百年来旧体诗创作的命运(写在《三益斋吟草》出版之际)
中华书局的编辑先生寄来新出的郑福田著《三益斋吟草》让我写点什么,我本与郑先生不相识,实在无从写起,谢绝再三,编辑以为我曾从事诗歌史研究,近来又发文谈今人所写的旧体诗问题,必有话说。待展卷读之,遂沉浸其
中,为其清辞丽句所吸引。这些作品不仅写得中规中矩,词采盎然,而且有情感、气韵流动其间,这对于今人来说是颇为不易的,因为许多人认为旧体诗这种形式已经死亡。
自从进化论传入中国,新学界大多数人也认同了文学形式不断演进,于是,就形成了新的体裁产生了必然预示着旧体裁的灭亡的结论。王国维先生在1913年撰写的《宋元戏曲考》的“自序”里,一开篇就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虽然王先生没有说唐以后无诗,宋之后无词,元以后无曲,然而这个只肯定“唐有诗”观念对后来新学者有很大影响,最典型的就是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写于1931年的《中国诗史》。这部著作中唐诗之后,紧接宋词,片言不及宋诗以及元明清诗;宋词之后紧接元曲,片言不及元明清词,似乎这些毫无成就可言。这是许多新文化人的想法,连鲁迅这样的大家也认为唐人已经把好诗写完,后人不必再在这种体裁上下功夫了。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
来信于我的诗,奖誉太过。其实我于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
不过这些都是新派文人的意见,大部分学者还不是这样看,文学史照样讲宋诗,许多辞章之士还在写旧体诗,因为那时凡是受过旧式教育都会写两句旧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旧式教育中《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诗韵合璧》等书就是教材,吟诗作对就是作业,而且诗歌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社会功用,朋友往来酬酢,就少不了诗歌,连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谈判都要带上一首《沁园春》,文士更是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技巧来学。由于还有读者,那时许多报刊上都有发表诗词的专栏,还有人对于当代诗词创作加以评骘,登载旧体诗词的报刊也多有连载的诗话或词话。鲁迅给杨霁云信中说到林庚白对他的旧体诗的评论就出自林在《晨报》上连载的《孑楼诗词话》。至于结社赋诗、雅集唱和,是许多有文化而又生活富裕人们所热衷的。有些雅兴很高并熟悉当代诗词创作的学者还做“诗坛点将录”或“词坛点将录”,把当代旧体诗人、词人按照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排列并一一加以评点,既是文学批评,又是文化游戏,好玩而且好看,如汪辟疆、钱仲联先生等。因此,尽管理论前卫,但现实生活还是由传统的教养和习惯支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干扰,各行其是。鲁迅是新文化的代表,可是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文人,他也未能免俗,既然“达夫赏饭”“闲人”只好“打油”,因此他不免要自嘲“言行不能一致”“自省亦殊可笑”。这便是文化多元下的生动景象。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社会转型,逐渐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方向发展,许多旧的文学体制受到质疑,旧体诗就是其中的一项。今人创作的旧体诗还算不算文学就成了问题?虽然没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讨论,但从当时的文学刊物来看已经把它摒弃出文学范畴之外,几乎没有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刊发旧体诗了。1957年1月《诗刊》创刊,第一期就发表了毛泽东主席旧体诗词18首与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信,对旧诗看法才有所改变。然而许多人还是认为只有毛主席的旧体诗是诗,是了不起的文学作品,这也只是个特例。因此旧体诗在文学领域一直是“妾身未分明”的。比如在我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诗歌史研究中从古代到近代的三四流的诗人也有人关注;而现当代诗歌史中的旧体诗的研究几乎是零,是没有什么人关心的。1957年以后,报刊上虽然偶尔也发表些旧体诗词了,但作者多是高官,或民主党派中的上层人士,即使偶有知识分子的作品(如苏步青、夏承焘、高亨等)出现,那是一种很高的政治待遇。不是什么人都能发旧体诗的。我没有见过普通作者或诗人的旧体诗出现在报刊上。编订出版旧体诗集更是一种极特殊的事情。最初只有毛主席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后来朱老总出版了《朱德诗选集》。“文革”中,朱老总受冲击,这也被视为“罪状之一”,理由是“毛主席出诗集,你也出诗集”。可见出版旧体诗集与诗人出版新诗集完全是两回事,诗人写新诗,出诗集那是文学领域的事儿,今人出版旧体诗集则是与政治有关的事儿,出版当局那是慎之又慎的。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不成文的条规被打破了;文革当中旧体诗逐渐走红,那是个冲突剧烈的时代,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人们郁积了太多情感能量,须要一吐为快,于是地下诗歌创作繁荣起来,而且旧体居多。1976年的四五事件是地下诗歌创作的一次总检阅,那首著名的“扬眉剑出鞘”就是代表。粉碎“四人帮”后,先是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天安门革命诗抄》(1977)、李锐的《龙胆紫集》(1980)出版;直到1982年,集作家、学者、诗人方面的聂绀弩先生的《散宜生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才标明旧体诗回归文学创作的殿堂。此书由负责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先生为之作序,表明主流的意识形态对它的认可。此后旧体诗逐渐从政治诗向多元题材发展,佳作不断出现,各地方出版社也有旧体诗集的出版,我见到过的就有数十种之多。郑福田先生的《三益斋吟草》也是其中一例。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还是由中华书局这样有影响的出版单位出版。
有百余年历史的中华书局,在建局的前四五十年里,是个综合性出版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也出版过《吴宓诗集》,这是个旧体诗集,吴宓是“学衡派”中坚,断不会写新诗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书局成为出版文史哲古籍的专业出版单位,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放弃专业的前提下有扩大出版选题的开拓。这次出版郑先生的旧体诗集大约是书局对于出版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尝试。
自文革以来旧体诗创作虽显繁荣,但由于大多数作者没有经过旧式教育,大多不懂旧体诗词是怎么回事,以为七个字四句就是七绝,八句就是七律,词也是按字数说。写作者或者按照毛主席诗词照猫画虎;或是在王力先生《诗词格律》或《汉语诗律学》格律规范下指导下亦步亦趋。这些作品名为旧体诗词,但没有旧体诗词韵味,在外人看来只是押韵的、有固定字数的文件。这就跟用西洋唱法唱京剧一样,旋律节奏都对,但唱的仍是歌而不是戏,因为它没有京剧的韵味。写旧体诗要有旧体诗的韵味关键是诗词语言文化的修养问题。
旧体诗词语言属于文言系统,但又有别于一般文言,它在用词方面不仅要考虑其本身的意义,还要顾及到语音(声、韵、调)、色彩,习惯的排列顺序,以及这些词汇所构成的意象。领悟诗词的精微之处还要靠多读作品和写作训练。我读郑先生的作品,感受最深的是他对传统诗词语言的熟练运用,他能够用这些处理自己要写的各种题材,这是一般受新式教育而又热爱旧体诗词创作的当代人很难完成的。当代人写旧体诗多停留在模山范水、写物抒怀、往来酬酢(当然这些写好了也不容易)上,因为这些大多有套路可循,四韵八句,起承转合,照此去写,大体不会离谱,过去受过诗词训练的几乎都是摇笔即来的。而郑先生的作品除了能把传统常见题材的作品写得格外精彩之外,还有大量写日常琐事的作品如其“童年琐忆”系列的《浣溪沙》中《占山为王》《夜看菜园》《说鼓书》《骑水裤》《打酱油》充满童趣,既有儿童的无忧无虑,又反映了乡村的贫困生活。特别是《打酱油》那首,现代人很难理解:
清酱沽来四五升,叫呼伙伴可同行。途长口淡饮于瓶。斟酌分人量出入,参差补水扭亏盈。归家莫怨可怜生。
乡村孩子平日没有零食吃,口淡,打酱油路途中偷喝酱油,这可能是城市小孩没法体会的。我曾在北京远郊偏僻山村呆过很长时间,那里老乡偶来北京,在小饭馆吃过饭,回家作为一个大发现向邻居宣传,到北京一定吃饭馆,那里酱油、醋随便喝,不要钱。酱油、醋在穷人看来是无上美味。孩子们偷喝酱油,又偷偷兑上了水,回家一顿苦打可能是免不了的。像这类无定式又充满新意的作品很多,词中有,七律、七绝中也不少。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本书“学海诗航”一集中感受作者学力及其运用诗词语言表情达意的能力。此集中无论咏史、月旦人物、品评名著多有真知灼见,又能以韵语出之,是为难。
啰里啰唆写了许多与本书有关或无关的话,以述近百年来旧体诗创作的命运,用以说明写作旧体诗词和出版旧体诗词的艰辛,也许与推荐本书关系不大,尚祈读者见谅。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